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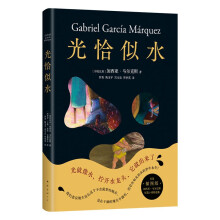







钟二毛小说的功夫很好,底层小人物的味道足够。写着写着就放松了,语言才华都释放出来了。
——韩少功
我们的小说在呈现变革时期乡村和农民命运的时候,有责任和义务在更深刻、更复杂、更有历史感的层面展开。在这一方面,钟二毛做了积极的努力和有效的探索。像《死鬼的微笑》《回家种田》这样的作品,在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中,都是不可忽视的。
——孟繁华
钟二毛写城市与人的小说,并不止于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人性的困顿与挣扎,犹豫与就范,觉悟与转变,这些复杂的面相,更是他写作所着力挖掘的。这个社会就像一个欲望的加油站,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心灵歧途和自我救赎?钟二毛以其敏锐与思力,发出了自己不同凡响的声音。
——谢有顺
面对瞬息万变、很难揣摩的时代,很多作家的写作选择了向内和私人化。观察钟二毛近些年的写作,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均以巨大的热情拥抱现实、直面现实。这是他区别很多作家的一个特点。描写当下,是很难的。钟二毛的努力似乎让人看到某种可能。
——梁鸿
钟二毛的小说在气质上幽默又忧郁,在形式上有精巧的变化与明快的节奏,在内容上触到了时代的脉搏和人性的奥秘。
——薛忆沩
钟二毛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收录了作者从事小说写作以来的五部重要作品。它们分别是《回家种田》、《死鬼的微笑》、《回乡之旅》、《无法描述的欲望》、《爱,在永别之后》。其中,《回家种田》获得《民族文学》2012年度文学奖;《死鬼的微笑》被改编成电影,并获美国第60届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小成本电影奖”。
回家种田
说来可笑又可疑,我每晚的梦里都装满了大片大片的稻田。这个时候,稻田已经落败,未割尽的禾根,在雨水和冷风的侵蚀下,近乎朽掉,人一脚踩上去,它们化成泥水。
偶尔,偶尔有一个老人会出现在田野上。我们在田野里机械地问候着辈分:伯,爷,太。老人问我,你一个人跑到田埂上来吹北风,搞什么卵子哦?我说,没搞什么,没事出来看看。老人又说,看条卵,你应该到广东去看高楼大厦。
老人围着我兜了一圈,走开了。他从家里走到田野里来,似乎就是为了和我说一句话。
正月初四一过,就有人搭车走了,说是再不走,车子就难搭喽,车费就翻倍喽。去早了,还可以拿到老板的大红包。他们走的时候,义无反顾,一大清早天蒙蒙亮背起行李就走,哈着白气离开,走起路来十分有劲。好像这个家,这个他们一砖一瓦一肩一膊垒起来的家,是一个旅店,住一晚就走,包都不用打开。这个时候,我好想冲出去,拦在他们的面前,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到底是哭是笑,是冰冷是热乎,还是别的什么。
我尤其是想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就是腊月初四一早走的,大年二十 九才回来。他们回来,没有给家里带来任何温暖。他们像是来开一个紧急会议,脚一进屋,就翻出各种东西,安排这样安排那样。父亲还向我要来本子和笔,把每天要干的事、见的人、还的账、交的钱一一列好,然后清早出门,晚上回来。大年三十晚上,他破天荒地打电话回来,说他在镇上,懒得回去了,今晚一家人到镇里的大酒店吃年夜饭,杀什么鸡宰什么鸭,今年搞点新鲜的。电话里,他十分兴奋,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感觉他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
极不情愿又充满好奇,一家人在冷风中走了五里地。一路上,炮仗声声,一刻也未断过,人像踩着嘣嘣声在走路。中间路过一片别村的田野。我绕进田埂上,独自走一条路。这片田野和我们月拢沙一样,死了。想找个禾根踩,都没有。
这么大片田野,没有一块种过东西,荒起。
整个田野,像一块陈旧的塑料薄膜,灰灰的,死了一般。
不是死了是什么?
母亲在喊我,快点走,要不你老子又要骂人喧阗了。
我赌气似的,隔着田野说,你们去,我不去了。
爷爷烟嗓子在嘶哑,你这个卵崽!
父亲看到我们来到,十分高兴。还是鸡鸭鱼,只不过酒店里是用盘子装的,家里用的是大海碗。服务员只有一个,也就是老板娘。老板娘还是个病人,看她右手扶着一个铁叉子,叉子上吊着一瓶药水,药水正一滴一滴地钻进她的左手。我怀疑一桌菜都是父亲自己端上来的,老板娘只负责喊一声“菜好了”。
在别人家里吃年夜饭,一切变得规规矩矩。父亲更像一个远道而来主持会议的人,大家都左右围着他坐开,母亲、我、爷爷、弟弟。
父亲说,大崽,过了年,你还不打算去广东打工?
我懒得回答。
父亲又说,哪个高中毕了业不都是去打工的?
母亲帮了一句,年轻人个个都在外面,你一个人在月拢沙干什么?那两块石板还没踩够?
那两块田有什么好种的?要田好种,大家早在家里种了。父亲接
着来。
年轻人要出去见见世面。母亲跟着又接了一句。
我就是想种田。我说。
请你别笑我。我真的是想留在月拢沙,种田,种稻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象一片田野蔓延着水稻的图景。夏天,禾苗出穗,风过处,青叶点头,还是瘪着的谷粒逐渐有了重量,禾秆由嫩黄变成淡黄。稻穗的味,清香。认真闻,没有,不经意鼻子一扫,又有了。
这个时候,一只绿背脊、白肚子的青蛙,在水田里跳跃,伸直的后腿,宣告它又消灭了一只害虫。
八月十五过后的二季稻秋收,惬意悠长。一年里的最后一季,不用像一季稻那样,被鬼赶似的,担心秧苗是否过老,担心旱情是否来到。早点去晚点去都没关系,一把细锯齿镰刀扫过去,五六坡禾苗倒下,握成一手,放在脚边,一起身,一块田被剃成了瘌痢头。喝口水,再蹲下去,再起身,身后的禾堆,纵横有序,像正饶有耐心地下一盘陆战棋。
脱粒后,谷子运回家,搬上楼顶。秋阳下,谷子翻身,晒干。晒干的谷子,味道不再是稻穗那种隐隐约约的清香,而是一股沉甸甸的香,刚脆的香,太阳底下的香。
再回到田野,禾苗变成了禾草。禾草也干了,把它锁起来!扯四五根禾草,做绳子,一掐,一绕,一紧,一顿,好了。一个小圆锥就站在田野上了。半天工夫,一块田站满了禾草小垛子。它们这回下的不再是陆战棋,而是活生生的国际象棋。
我种过水稻。高中毕业后的夏天,我在爷爷的帮助下,跳过一季稻,插上二季稻。
是的,只有年过七十的爷爷帮助我。
整个村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孩。
我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十八岁。
我们是农民,为什么让田野荒废?
我问爷爷。
月拢沙 叶梅 /1
回家种田 /1
死鬼的微笑 /14
回乡之旅 /26
无法描述的欲望 /38
爱,在永别之后 /116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