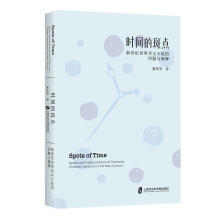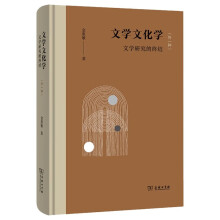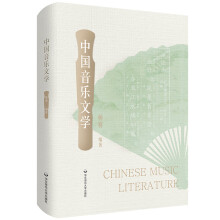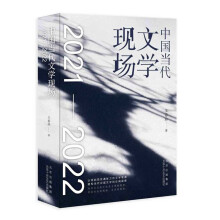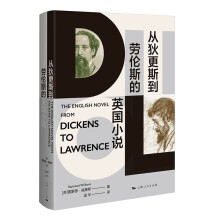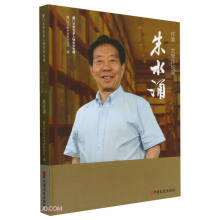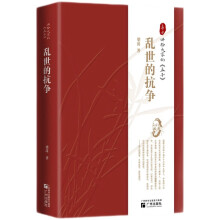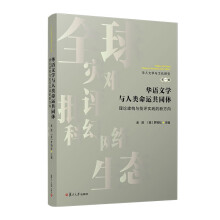《美国犹太裔文学研究论集/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丛书》:
《贝拉罗莎暗道》的核心故事,是有关大屠杀幸存者方斯坦的叙事。它构筑了整个小说发展的基础。方斯坦是一个波兰犹太人。二战期间家人大都被纳粹杀害。他在意大利集中营被一个叫“贝拉罗莎”的秘密救援组织救出。在被救助过程中,知道了该组织是美国娱乐界大亨犹太人比利·罗斯设立。因此,很自然,当他几经辗转登上新大陆并过上幸福生活后,他想见见这位救命恩人并说声“谢谢”。于是,这个颇为人性化的朴实愿望给他带来一场场精神陷落:寄出的信被一封封原样退回。他怀揣感恩之心去比利办公室被挡驾,又寄去支票请比利把钱转给慈善事业,但支票也原张退回。一次在一家饭店看到比利。他不顾一切地隔着阻挡他的人向比利喊道“我是来告诉您,是您把我从意大利救了出来”,但比利转身面朝包厢的内墙,方斯坦则被赶到街上。
小说的重点叙事不在大屠杀本身。而是表现大屠杀之后一些相关的人面对它的态度。显然,这里面出现历史连接与断裂的纠葛:于方斯坦而言,大屠杀是一段黑云压顶的族类历史和人性灭绝的灾难,是生命中不可忘却的重。他站在种族历史的废墟上,希望在一种朴实的人性维度去感恩,表明对方付诸危险所救助的这个生命,已经真正活下来并懂得救助的人性含义,正在试图用行动(比如捐助)把这个意义的链条连接下去。因此,他是以幸存者的身份,在见证历史灾难的同时,也见证人性的不可毁灭性。感恩不仅仅意味着知恩图报,而是性命与人性经历严酷劫难之后的温暖表达,证实着阳光在心里的不曾消失。这应该属于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道德行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故事的讲述者索莱拉——方斯坦的妻子——才愤然挺身而出,不屈不挠地寻找各种机会,在丈夫“失败”的终点起步,谋求比利和丈夫见面的可能。索莱拉也是犹太人后裔,是小说的重要角色,既是方斯坦故事的讲述者(听者是他们的犹太亲戚),也是方斯坦故事的后期参与人。重要的是,无论讲述还是参与,在小说中都有浓重的人性道德判断意味。索莱拉和他们的犹太亲戚对此事的共识是:比利也是犹太后裔,和方斯坦隶属一个群体。在大屠杀历史中曾经写下光辉的一笔,说明了他的族类感情。因此没有理由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割断历史;而和方斯坦的“见面”,已不单单是一方感恩和一方接受的问题,更是族类历史和人性道德的一种延续方式。而且索莱拉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中出现如此恐怖的屠杀事件,人的尊严和生命在大屠杀中如此被糟践,谁还有权利不去正视呢?更何况是犹太人自己?正视大屠杀是人的尊严问题,人们不应该因为事件已经过去就该遗忘。正是这样的价值思考奠定了她的顽强态度,使得丈夫与比利的见面在小说中成为一个“历史记忆”的象征。
如此看重民族历史以及族类人员之间的亲近关系,是犹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犹太学者赫茨曾经说过:“任何犹太个体都是犹太群体的一个成员”。这来自他们对上帝创造的原初家庭的坚信不疑。第一个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注重的即是“关系”,即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亲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努力在其中建立一种爱的道德结构(moral structure)。因此,犹太教除了对上帝的信仰,还有它较为世俗的一面。与祖先、邻里的关系也是他们在人世间建立人道结构的重要部分之一,并成为一种道德观念扎根在文化价值深处。另外是对生命的看重。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的礼物,是神圣的,应该在人世间过一种道德与尊严的生活。于是生存便成为一份道德责任。这也是这个民族历尽磨难流散世界各地却依然顽强地存活下来,并出现数不胜数的杰出人物,在各个领域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这些信念因素延伸出了犹太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当希特勒处心积虑地试图灭绝这个民族时,曾经有纳粹哲学家首先在哲学上论证人道主义精神的过时性,认为那是过去时代的产物,20世纪是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哲学精神云云,作为纳粹反人类行动的哲学基础。
因此,无论是从重视族群关系而言,还是从重视生命角度而言,于犹太人都是一份大责任,这也是本小说的价值出发点。而小说中的比利·罗斯,这位做出惊人事迹的人,事实上却与犹太道德价值观念相去甚远。他在索莱拉断续的讲述中逐渐显现出的面目十分繁杂:在百老汇做过制片,投机过房地产,禁酒期间做过某黑帮生意的合伙人,还组织雇用一个写作班子专门为报纸写“闲话”专栏。私生活乱七八糟,由于性屈辱和女人有各种纠葛,为了一毛钱也会大喊大叫等。无论哪方面,“事业”还是生活,大体和犹太传统道德背道而驰。用听者“我”的说法,是一个典型的“浑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