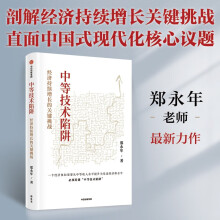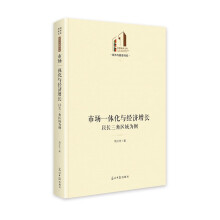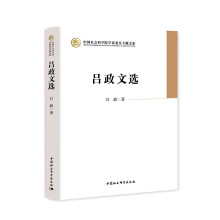显然,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设置, 基本动因是上海出于
打造扩大对内开放的核心承载区, 更好地平衡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
之间的关系, 更好地发挥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中的龙头作
用。 这也正好说明, 过去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 上海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龙头作用, 主要体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
而在对内开放的引领作用发挥得不够, 既没有形成面向长三角和长
江流域的核心承载区, 没有一个对内开放的载体, 也没有系统化的
制度性的对内开放体系。 一些让上海享受的国家战略优势和具体的
优惠政策, 也大多是从强化其国际经济、 贸易、 金融、 航运中心地
位的角度去设计的, 不仅长三角其他地区无法复制和享受, 而且对
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产生了严重的虹吸和极化效应。 这其中的主要
原因有三:
一是与国家出口导向型战略的趋势推动有关。 1992 年浦东开
发开放, 尤其是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 我国发展战略的空
间指向是向东开放, 面向蔚蓝色的海洋, 加入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
国跨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以加工出口、 利用海外市场驱动发
展。 因此这个时期的对外开放就是发展, 对外部市场利用的重要性
大于利用国内市场, 对外开放的紧迫性大大高于对内开放。 这就不
难理解, 在这个时期, 上海不会把扩大对内开放作为工作的重心,
不会放到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 不会去想如何建设好与长三角其他
地区的协同机制问题, 更不会去主动考虑建设链接苏浙皖的核心承
载区。
第一章 实施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国家战略 13二是与中心和周围关系的发展阶段有关。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内核是上海。 这与国内其他地区如京津冀、 珠三角有很大的不同,
后者要么去中心化如北京去 “非首都” 功能, 要么缺乏明显的中
心, 而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公认的龙头。 上海与周边的江浙皖地区存
在长期稳定的 “中心 外围” 关系, 在发展上总体处于极化资源的
阶段, 表现为上海除了转移了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外, 在
大多数时期都是极化能力高于扩散能力, 强烈地虹吸全球、 全国尤
其是长三角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和资源。 因此, 如果说一体化发展
就是要苏浙皖对接上海, 那么在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情况下,
各地就既想通过对接上海获取溢出效应, 又担心自己的发展势能被
上海虹吸。 这样, 各地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矛盾心理和谨慎
措施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
三是与分散化竞争的转轨经济体制有关。 1978 年以来我国以
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 塑造了利益边界十分清晰和相对独立的地
方政府主体, 它们深度地参与经济运行, 对经济干预的程度很深。
这一格局使其可以利用行政权力干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 从而
出现各种反市场一体化的倾向。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上, 上
海虽然一直是各地口头上坚决承认的 “龙头”, 但是各地出于自身
利益的考虑, 心底里却都在打各自的 “小算盘”。 过去, 即使是上
海自身, 也被其他地区抱怨为 “不像大哥的样子”。 尤其是邻近的
江苏, 由于关系到一体化发展的最基本的跨地区基础设施, 也存在
很多的 “断头路” 等不通畅的问题, 所以说起一体化发展便非常谨
慎。 如长三角地区的机场建设问题, 由于全球IT 产业主要集中在
苏南特别是苏州工业园区一带, 因此江苏方面非常希望虹桥机场能
够建设更多的国际航线。 但上海方面的决策是建设远离江苏南部的
浦东国际机场, 于是江苏不得不修建了苏南的硕放国际机场, 但很
快上海又回过头来建设虹桥枢纽。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