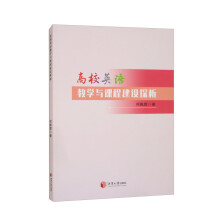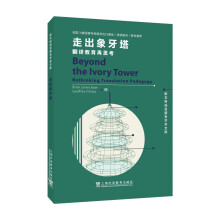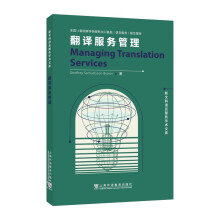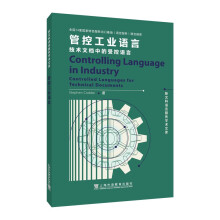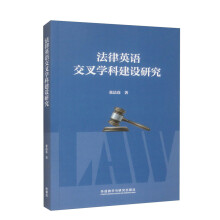《后语言哲学论稿》:
1.理论背景
1.1 中国哲学向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上的转变
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近十年来,我们见证了分析哲学急剧发展甚至可以说是繁荣的局面。
我们有必要就中国哲学家的研究方法来做一个简要的反思,因为过去的研究方法深深影响着现在对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江怡指出,第一种传统方法可标签为引进与梳理,已故著名哲学家胡适使用的就是此法。此类哲学家的行动纲领事实上是“我注六经”。循此路径,现代哲学家涂纪亮、江怡与朱志方等人对分析哲学遵循着引进与梳理的模式。第二类策略可标之以分析与批评,已故的深有影响的哲学家冯友兰常用此法。循此路径的现代哲学家有张志林、陈嘉映以及徐友渔等等,对分析哲学采取了分析与批评之法。第三类可表述为“深入阐发”。事实上,第三派哲学家的纲领是“六经注我”。诸如叶秀山、周国平等当代哲学家遵循此法。他们主张,哲学是为哲学家服务的。他们抓住西方哲学的话题,专注于发挥自己的思想。有时,他们的发挥甚至超出了西方思想的本身。更有甚者,他们“故意地误解”(不是贬义)西方哲学。本文作者提到这三类方法,本意不在分出优劣,我们不能阻止任何人从上三者中选择其一。比如江怡择其一与二,因为他认为前两者是真正地研究西方哲学。我们相信,此话不虚,但谁也不能否认第三类是启发思考,虽然有时这种思想的引发有点偏离了西方哲学的轨道。
中国哲学家并不认为对分析哲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他们直到目前为止所采用的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主要还是来自西方。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用分析哲学所特有的方法来处理分析哲学。在中国,一直流行着所谓的“跟着说”,然后是“接着说”。江怡认为,这一路子是引进分析哲学的方法,不是研究分析哲学的方法。我深以为然。
江怡(1999)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实证原则与科学精神的缺乏,毫无疑问会使分析哲学的研究跟着别人走。这就是为何我们过去的分析哲学主要是引进与介绍而无原创、为何我们不能直接与西方分析哲学家对话的原因。但是,近十年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作者提请读者注意“不能直接与西方分析哲学家对话”这一措辞。正是为了扩大这种直接对话,本文作者才在本文详细地介绍今日之中国出现的“后语哲”的情况——一种尝试性的对待经典分析哲学的进路。
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说中国搞分析哲学的哲学家有自己的方法的话,那么这便是强调概念分析,而不是逻辑分析。精细地梳理一个概念的意义,真正地弄清一个命题,是分析哲学之为分析哲学的真谛。概念分析的代表人物是张岱年,其代表作是《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1989),而逻辑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江天骥,其代表作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1984)。
在严谨地观察了概念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结合之后,江怡在他的论文集《思想的镜像》中提出了他所谓的“哲学拓扑学”(PhilosophicalTopology)。“哲学拓扑学”奠基于逻辑分析而不是概念分析。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思想本身从逻辑上搞得更为清晰,更为有效。江怡认为,概念分析要求的是表达明晰,而逻辑分析要求的是表达的有效性。另外,他说,我们要特别注意以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方法,特别是分析哲学中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哲学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取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想。
我们都知道,只是在不久以前,哲学仅仅是大学哲学系或哲学家的事情、与外语界教师无关的状况才开始改观。
1.2 中国:从做分析哲学的特别范式到后语哲
在我看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几乎是一回事。我这样说的依据是,《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Bunnin&Yu,2001:755)说:“近代语言哲学由哲学的语言性转向引起,其基础是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的哲学分析都可归结为语言分析。广义上而言,语言哲学几乎是分析哲学的同义词。”他们的看法与我的观点合拍。
同时,“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可以与“语言的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互换,后者强调的是分析传统。
一般地说,“语言哲学”涵盖了英美传统的“语言的分析哲学”与欧陆阐释传统的语言哲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做分析哲学的特殊范式,即,一部分人偏向分析哲学,另一部分人偏爱语言哲学。这种区分看起来真是有点奇怪,但自有其缘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