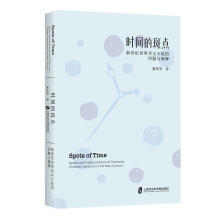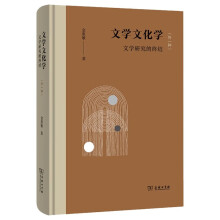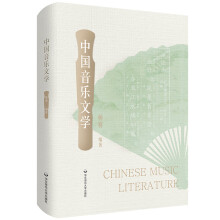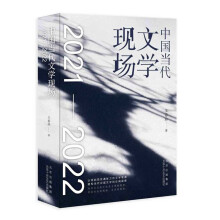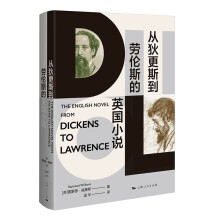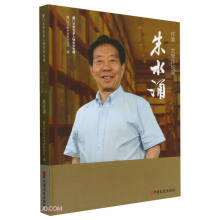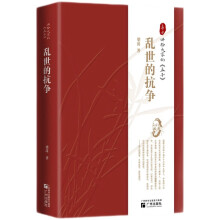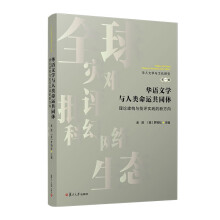《中日现代诗歌比较》:
这首诗塑造了一个慈爱的母亲形象,叙述一个农村妇女在听到自己的孩子死于战争时的悲伤情感,是一个母亲所谱写的一首悲恸的歌曲。从母亲的歌曲里,我们读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底层人民悲苦的生活以及农民的绝望情绪。在壶井繁治的笔下,这些农民形象手无缚鸡之力,在沉痛的渊底等待他人的救助,不像蒲风笔下那些带有悲壮色彩的形象具有英雄气质,而显示出消极颓废的色彩。
朱光潜在《诗论》中说:“心中只有一个完整的孤立的意象,无比较,无分析,无旁涉,结果常致物我由两忘而同一,我的情趣与物的意态遂往复交流,不知不觉之中人情与物理互相渗透。”②情趣可以是诗人的,也可以是读者的,形象是一种物的意态,形象是诗人抒发情感的载体,也是诗人某种气质的表象。
中国左翼诗人笔下的农民形象所带有的英雄气质是诗人英雄情结的体现。周作人曾指出:“英雄崇拜在少年时代是必然的一种现象,于精神作兴上或者也颇有效力的。我们回想起来都有过这一个时期,或者直到后来还是如此,心目中总有些觉得可以佩服的古人,不过各人所崇拜的对象不同,就是一个人也会因年龄思想的变化而崇拜的对象随以更动。”“英雄情结”伴随着大多数人的人生旅程,深潜于人的意识之中不可消磨。诗人所固有的英雄情结、英雄崇拜的潜意识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被唤醒,往往把自己所固有的英雄气质投射到笔下的形象,通过形象性格和命运的展示,表达诗人自己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在蒲风的笔下就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如《农夫阿三》中阿三的精神面貌正是诗人英雄气质的显现,诗人借助阿三的行为来告诫自己不要逃避战争,不要逃避苦难,且告诫同胞们要正视苦难,希望所有的人拿起枪,对准敌人的头颅,但是现实却没有为他的抱负买单。
日本诗人的英雄情结较中国诗人而言显得弱一些。在日本诗人笔下,他们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是悲情的,正如壶井繁治在《声音——一个母亲的歌唱》中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她听闻孩子的死讯后陷入悲痛之中,听到外面虫鸣误以为是自己的孩子在呼喊,甚至联想到自己的孩子将死的场面。诗人描写一个母亲想象自己的孩子被杀场景的残酷,正是这种残酷烘托出了一个悲情的形象。从这首诗歌里,我们也窥见了诗人潜藏在心里的巨大悲愤,强烈谴责战争,同情底层人民。
综上所述,中日左翼诗人都塑造农民形象,中国诗人笔下的农民犹如一个悲壮的英雄,在黑暗的社会里奋起反抗,苦于现实的压迫而失败;日本诗人笔下的农民却带着强烈的悲情色彩,反抗意识薄弱。人物形象往往是诗人情感的表现,在这些人物身上往往赋予了诗人自身的特点。中国诗人潜藏的英雄情结“化身”在诗歌人物形象上,他们敢于反抗的精神正是诗人自己英雄情结的体现,诗人希望充当时代的改造者,改变农民的生活处境;在日本左翼诗人那里,他们通过展示对弱小群体的关怀来显现英雄气质,在诗中更多的是倾注自己的情感因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