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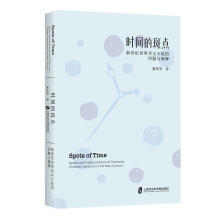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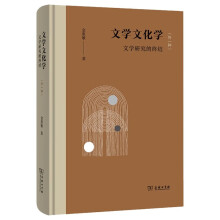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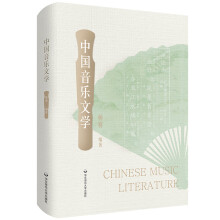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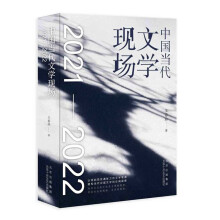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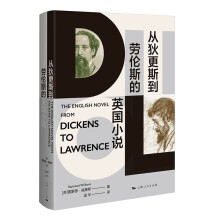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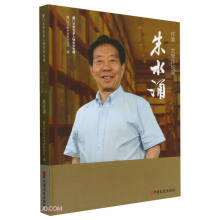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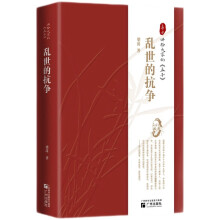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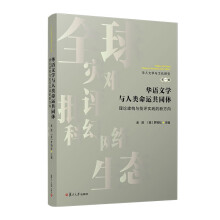
本书重点叙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文学本身的一“缩”一“胀”: “缩”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日益边缘化,文学已经很难借助自身的力量或业内人士的运作引发社会的关注,创造合理的收益;“胀”则指的是文学因素藉由大众传媒、出版、影视、广告等主流媒体的运作,外扩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变化导致了“文学”的重新定义,以及文学在社会生活的重建,从传统文学的定格化,到网络文学的崛起与演变,再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新的文学需要新的描述与新的研究,它是如何生成与转型,又有何种的生机与困境。本书尝试勾勒这一转型时期的图景。
本书探讨的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媒环境日趋多元化的情形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不同于此前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浓烈的政治色彩,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受到从西方涌入的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其自身已步入一个“多元杂语时代”,又在资本的运作和以出版、广播、电视、电影为主导的大众传媒的引领下,蔓延至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身的走向亦发生了变化,与传统文学发展路数分道扬镳。这种变化导致了“文学”的重新定义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建,作者试图勾勒的便是这一转型时期的文学发展图景。
欲望的反噬:结局早已注定
思想解放伴随着改革开放而生,文学是阵营中最显眼的一骑,背后站着文化、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所有的战骑汇聚成了一个最强音,那就是:证明欲望的合法性。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肯定个人肯定欲望,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主旋律,不管这个欲望被书写成美好的,合理的,自由的,传统的,都因应着此前对欲望的压抑,个体的束缚。欲望的释放是社会的需求,整个社会都在产生一种巨大的变化。文学借助历史和现实的书写,在整个社会争取个人欲望表达与个人权利获取的斗争中,承担着主要的角色。
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社会对欲望的追求已经势不可当。无论善恶,无论美丑,真实的欲望已经拥有了绽放的机缘与理性的肯定,这种追求已经无须借助文学的加持与修饰。
相反,恰恰是在这种对欲望的全民性追求当中,无法直接产生物质利益的纯文学,开始退居精神生活的边缘。
这是之前虽然为个人欲望摇旗呐喊,但始终坚持某种非功利与审美谈起的纯文学始料未及的后果。19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精英角色的改变,与精英心态的失落。从今往后,文学再也没有了新时期的中心位置。
这个节点伴随着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港台文学的大举侵入,伴随着张恨水、王度庐为代表的民国通俗文学的复兴,当代文学处在一个巨大的裂变之中。1997年正是这样一个分裂点,在这一年,王朔用作家与影视的完美重组,完成了新时代世俗文化的初步塑形,这一年汪曾祺与王小波的去世,象征着民国文脉的断裂,西方文学思潮的式微,中国文学走到了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而抉择,几乎早已注定。
个体,大众,欲望,市场,这些当初中国当代文学曾经为之摇旗呐喊,苦苦追求的语词,变成了挖倒文学中心舞台的挥锄手。“纯文学”不再担当精神生活主流和启蒙民众的导师,占领它留下的权力真空的,是那些充斥着娱乐意义而规避教化色彩的文化产品。它们甚至不再以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的传统形式出现,而是更具冲击力的视觉图像,迅速提供精神刺激与心灵抚慰。1990年代初期,精神生活的聚光灯属于《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以及绵延十载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它们成为了中国精神生活的主流,也形塑着后来城市娱乐的雏形。
高原与高峰:遗产或债务
新的局面,将中国文学逼到了一个非变不可的境地。19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中国文学的先锋化与随之而来的世俗化,其实也可以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先锋化与世俗化基于同样一种焦虑,即“文学”需要从“文化”、“人文”这样的大概念中蜕变出来,标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特性。
先锋化是通过极致的语言实验与叙述探索,包括对西方文学各种流派的引进与模仿,将文学塑造成一种与大众隔绝的高端艺术形式,以晦涩与多义为门槛,将文学抬高为专业化的智力游戏与精神品类。先锋文学的实验与探索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依仗诗歌、实验话剧与艺术电影不绝如缕,也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分众时代。
世俗化则是用文学搅拌娱乐,向大众赋能的一种狂欢。世俗化的主体是受众,作品与作者都像是屏息待命的手工艺人。1980年代的光环在二十年内慢慢消耗,让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刘震云屹立不倒,而他们也在悄然完成着世俗化的转向。新文学的遗产与世俗化的包装,遮掩着这种主体的替换。
进入新世纪十年之后,不管是学界研讨,还是官方评判,似乎都形成一个共识:当代文学“有高原,无高峰”。每年都有说得过去的重量级作品,但就是缺乏配得上伟大时代的文学杰作。这种状况的出现,恰恰是当代文学发展至今,接收的遗产与债务的共同体现。
经过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创作浪潮,从反转镜面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到先锋化的语言实验,世俗化的市场磨合,当代文学在结构谋划上,在语言技巧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筚路蓝缕的现代白话文学。一大批1980年代之后成名的作家完全足以源源不绝地贡献出水准线以上的诸般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无不如此。
但不可否认,纯文学涵括的诸般门类,当它们面对现实和历史的书写,都显现出某种程度的疲惫无力。根源或许在于作家对于这个社会的结构变动已经无法全面感知——这种观点似乎能解释为什么为现代汉语提供了典范式语言的汪曾祺,在解答“为什么总是写旧社会”的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无奈:
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桥边小说三篇·后记》)
这或许是新时期成名的一大批作家共同的心声。对社会结构的难于理解,面对现实生活的难于沉潜,让面对乡土与往事横刀立马的成名作者们,在都市与现实面前纷纷败退。惯性而不失水准的写作,是谓有高原。茫然而乏力的攀登,是谓无高峰。
当代文学所谓“有高原无高峰“的外在性原因,也是文学的边缘化位置。文学作品与主体受众之间,缺乏互动与感应,彼此之间倒是充斥着误读与歧见。大山不辞细土,没有时代的呼应,高峰只能是记忆与想象中的海市蜃楼。
骑士怎样变成剧团:
——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代序)
骑士与剧团:蹩脚的寓言
欲望的反噬:结局早已注定
高原与高峰:遗产或债务
膨胀与狂欢:碎片化与分众化
引言:文化转型与文学重生
——分期与征候式人物
第一章 社会转型期的文学震荡
第一节 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文学现象
第二节 海外文艺与文化思潮的冲击
第三节 众声喧哗:思想大论争
第四节 从中心走向边缘
第二章 世纪末:边界的探索
第一节 “新”字号小说的浪潮
第二节 王朔:《顽主》承载时代情绪
第三节 王小波:《黄金时代》引入“狂欢传统
第四节 陈忠实:《白鹿原》展现”民族秘史
第五节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英雄情结
第三章 新世纪的钟声:终结与重生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传媒时代的困境与生机
第二节 “莫言获‘诺奖”’的八个关键词
第三节 逃离中的陷落:网络小说体制中的资本元素影响
第四节 回响:晚清小说与网络小说异同辨
第四章 寓文于乐:文学元素的外扩与渗透
第一节 评价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
第二节 《色,戒》引发的文化震荡
第三节 “话题电影”在中国的兴起与出路
第四节 城市娱乐:显形与失魂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