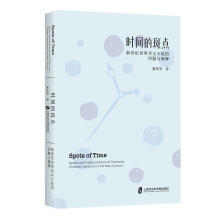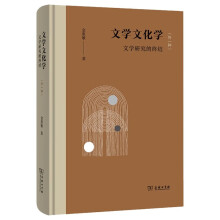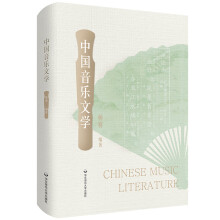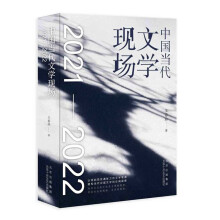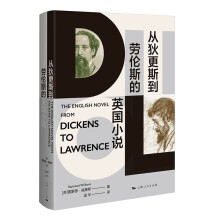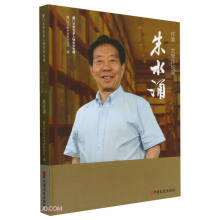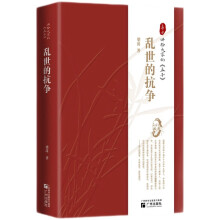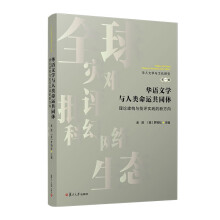《钱穆文艺思想研究》:
钱穆非常看重编年集、编年诗文的价值与意义。他说:“中国文学家乃不须再有自传,亦不烦他人再为文学家作传。每一个文学家,即其生平文学作品之结集,便成为其一生最翔实最真确之一部自传。故日‘不仗史笔传’,而且史笔也达不到如此真切而深微的境地。”①作家既与作品融凝合一,其作品乃成此作家之自传,将其诗文编年排列,即成为作家的年谱。杜诗既是其个人人生一部历史记录,同时也是时代人生的历史记录,将杜诗编年,便可当得杜甫生平年谱;而陆游晚年几乎日日有诗,抒写日常人生情意,“使读其诗者,不啻如读其当时之日记”,亦是陆游当时一部年谱。中国文学史上杰出诗人,只要是儒家,“每一人之诗集,即不啻是其一生之自传”,而“一诗人之自身生活,即不啻是一部极佳文学作品”。②进一步说,如果作家诗文集缺乏为之编年的必要,那就足以说明此作家尚未达到作家与作品合一的理想境界。
钱穆指出,中国文学以人为本,强调在作家与作品之上有一共通标准,即牵合文化生命而表演于政治意识之“雅”的标准,而作家的标准更高于其作品,因而中国文学必求能于作品中推寻其作者,由作家个体人生见出时代人生与文化人生。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学不朽,其实主要条件乃在作家自己内心德性人品的不朽,而作品行世、存世,也主要依赖于作家的人文修养,作品乃附于作家而流传。
作家与作品合一也就是文学与人格合一,同时也是性情与道德合一。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一种内倾型文学,强调将外在人生事件转化为内在道德性情、修辞技巧转化为人格锻炼,一切只在人的心生命中开展,以融凝和合于文化生命大传统为归宿。“此种文学,必以作家个人为主。而此个人,则上承无穷,下启无穷,必具有传统上之一种极度自信。此种境界,实为中国标准学者之一种共同信仰与共同精神所在。若其表显于文学中,则必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乃始可达此境界。而此种境界与精神,亦即中国文化之一种特有精神。”睢有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作家的文学生命乃能在人生道德性情的根源处与文化生命发生共鸣,此是人文修养的最高理想境界。
文学与人生合一,作家与作品合一,乃是“诗史”精神的内在要求,作家的人文修养惟有到达此一境界,其作品方可担当起“文以达心”的人文使命。浦起龙《读杜心解》卷首《读杜提纲》云:“代宗朝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所谓“诗史”并不是所写句句、事事都与史实相合,其主要精神当在“显出一时气运”。钱穆对“诗史”精神的阐发,主要亦着意于“气运”,强调文学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的责任。他说:“一个理想的文学家,首该了解此人类社会之整全体。此整全体即为人生道德与人生艺术之根源所在。……而一理想的文学家,又必须在其自身生活中,能密切与此整个社会相联系,必期使此社会种种变故与事相,均能在此文学家之心情与智慧中,有其明晰而恳切的反映。而此种反映,又必能把握到人心所同然.这始是理想文学作品之真来源。”钱穆将“诗史”精神阐释为文学家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种责任,强调这正是“文以达心”的根本纲领,中国文学人文使命之种种具体要求皆渊源于此。
非惟文学,中国艺术亦具此种“诗史”精神。“诸艺术中,惟音乐为最切于人生,以其与人心最能直接相通。故音乐不仅能表现其人之个性,而尤能表现时代,于是有‘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之分别。”音乐在表现人生、人心的同时,折射出时代状况,往往能勾画出“史笔不到处”。“又如京剧中有锣鼓,其中也有特别深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