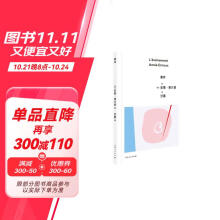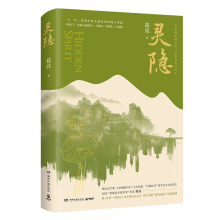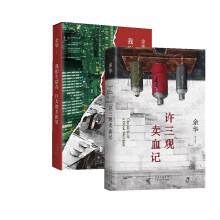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像纸片一样飞阳光下的故乡/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第一章
下午四点,阳光仍旧灿烂,甚至更烂漫了。西天的霞光浩浩荡荡奔涌而来,把整个城市涂抹得像一个浓妆艳丽的女人。这个时刻的它开始不安分了,有了蠢蠢欲动的念头,有了一点儿淫荡的味道。
不过,何一为却没有心思和兴趣体会城市在一天里的细微的变化。他急匆匆地赶路。马路上已经有了落叶,是法国梧桐的叶子,宽大而明亮,很像是虚拟的油饼,一张张的,无序地铺排在还算洁净的路面上。走着走着,他眼前一亮,停下来。
估计就是这儿了。
在九月依旧逼人的阳光里,何一为费力地仰起脸来,望着面前这座高大雄壮的建筑物出神。不断有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小轿车从何一为身边唰唰地驶过,带来一股股混合着浓烈汽油味的热风,在他身前身后旋转奔突。约有一个足球场般大小的广场上,除了停泊得整整齐齐的小车,便是摇来摇去的红男绿女,偶尔有一两个身着深蓝色制服的保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他们的整束很像军阀混战年代的仪仗队员。大厦门前的喷水池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仿佛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消失的梦境。
何一为来到省城刚刚半个月。他身穿纯白色的的确良短袖上衣,下身着一条深蓝色的长裤,脚蹬回力牌白胶鞋,衣服由于换洗不及时而染上了淡淡的汗渍。他的头发长而凌乱,眼神飘忽不定,流露出一种怯怯的成分,明眼人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外地人。
何一为来自离此五百里外的一座小县城,他考上了省城一所最著名的大学。半个月前,他走下长途汽车,双脚刚一踏上省城的柏油路面,心里就咯噔咯噔响了一阵,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由表及里,狠狠咬噬着他。后来他想,他有这种感觉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他原本就是这座城市的人。十六年前,他们全家搬离了省城,从此他就与这座城市断绝了来往。但现在,他又来到了这里,他不知道自己以后的路怎么走,他只知道他是作为一个外地人闯进这座城市的。
这座城市会接纳我吗?会接纳我吗?他一遍遍地想这个问题。到后来又变成了他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能喜欢上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吗?
他得不到任何答案。
他们全家搬离省城的那一年,何一为才五岁多一点儿。在他闪烁不定的记忆中,他家住在城东靠近市中心的剪子巷。那是一条曾经挺有名的巷子,一切都显得古色古香。剪子巷19号就是他的家。那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是他的祖父在这座城市刚解放时,用攒了一辈子的钱买下来的。祖父祖母去世之后,房产就落到了他父亲名下。到这时,房屋都很破旧了,屋顶上的瓦缝里长满了荒草,风一吹过就发出沙沙的响声;院子倒挺大,铺着青砖,由于年深日久,青砖早变成了土地一样的黑褐色;院子中央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洋槐树,每年春夏季节都有一些“吊死鬼”拖着长长的丝线晃来晃去,稍不留意,它们就会钻进你的脖颈儿里。那时,年幼的何一为没有朋友,他就捉“吊死鬼”玩,有一天,他捉了满满一洋铁盒,又把它们放进了父母床上的被子里。晚上睡觉时,他的母亲被满床的肉虫子惊呆了。他的父亲气得咬牙切齿,照他屁股就是一巴掌,然后又怒气冲冲地说:“我他妈的早晚要亲手刨掉这棵该死的洋槐树!”
然而没等他的父亲实施刨树的计划,他们一家就给撵到了五百里外的地方。后来在父亲最悲惨的日子里,有一天父亲突然说:“也不知咱家那棵洋槐树咋样了,我很想念上面那些‘吊死鬼’……”
母亲冷笑一声,接过话茬儿,恶声恶气地说:“你还有脸提这些!我们混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父亲叹口气,说:“是呀,我他妈的连那些‘吊死鬼’都不如啊!…一”
他们家一系列的不幸的变故完全与父亲有关。是父亲一错再错,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
半个月前的一天傍晚,二十二岁的何一为扛着简单的行李走下长途公共汽车。下车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路边的一个小摊上花五角钱买了一份省城导游图,然后他借着路灯昏黄的光亮迫不及待地仔细研读,但他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剪子巷。到学校报上到后,他又找人打听,有谁知道剪子巷在哪儿?系里的一位副教授说,他在本城待了十多年,从没听说过有这样一条巷子。何一为当然不死心,继续找人打听,甚至不惜跑到学校图书馆翻阅省城十多年前出版的旧报纸,企图从那上面找到答案,终是一无所获。直到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在校门口摆摊修鞋的一位老大爷告诉他,先前城里确实有一条名叫剪子巷的小胡同,离市政府不远,但“文化大革命”时改名叫红卫巷,“文革”结束后又改名叫青年路,那地方不难找,因为本城最高的大楼——五星级的金鼎大厦就矗立在那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