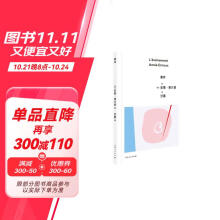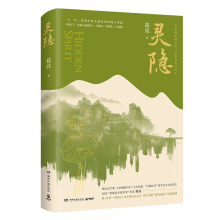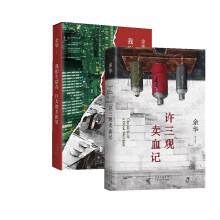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落失男孩》:
光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喷泉激泻而出的羽状水柱潺潺搏动,再让四月的徐风吹成广场上一片细如蛛丝的虹彩水雾。消防局的马匹以其僵硬的步子往地板跺响足音,态度漫不经心得很,那干净的粗尾巴也会配合甩个一两下。每隔十五分钟,路面电车便伴着刹车声打四面八方缓缓驶进广场,然后按照惯例暂停片刻,犹如装了8字形手扭的发条玩具。广场对面,报废车回收场的老马正努着劲儿拖着一辆板车,嘎哒嘎哒地穿过他父亲铺子前的鹅卵石路。下午三点了,法院大楼的钟即刻叩出庄严隆重的报时声,然后一切又是老样子。
他用那双安静的眼看着这盘形状恼人的哈吉斯——这座广场是由一砖一石撞出的残破街景,是由风格迥异、互不搭调的各式建筑拼合而成的大杂烩,但他没有因此感到失落。因为,“这儿,”格罗佛心想,“这儿就是广场,广场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这儿有爸爸的铺子、消防局和市政厅、潺潺搏动着羽状水柱的喷泉,有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光,有嘎哒经过的旧板车、报废车回收场的老马,有每隔十五分钟便会驶进广场、然后就地暂停的路面电车,有五金行坐落在那头的街角,有五金行隔壁那设了塔楼、屋顶还筑了城垛、外观宛若古堡的图书馆。这儿有整排的旧式砖造楼房沿着街道这一侧林立,有路过的人和来来往往的车辆,有来了,然后发生变化,但始终会再出现的光,有来来往往,并在这座广场发生变化,却依旧会返回原样的一切——这儿,”格罗佛继续想着,“这儿就是永不改变、始终如一的广场。这儿就是一九O四年的四月。这儿有法院大楼的钟和下午三点的钟声。这儿有侧背着送报袋的格罗佛。这儿有老格罗佛,快满十二岁的格罗佛——这儿就是恒久不变的广场,而格罗佛在这儿,他父亲的铺子在这儿,时间在这儿。”
因为在他眼里,这座二十年来始终维持着又是砖又是石,偶将时间和断裂的心血之作聚拢成堆的广场,即是他小小宇宙的小小中心。在他灵魂的图像里,这座广场即是地球的枢纽,是弥久不变的花岗岩岩核,是尽管人事来来去去,也仍守着永恒,永不改变的经常之地。
他走过街角的旧棚屋。这间木造房屋盖在容易失火的消防死角,是S.戈德博格卖法兰克福熏肉肠的摊子。然后他走过摊子隔壁辛格家的店。店里陈列着光洁闪亮的新机器,引人人胜的日历上展示出辛格家的厂房——有漆着令人心潮澎湃的红色的大型建筑物,有绿得让人难以置信的青草地;讨喜的载货火车由模型玩具一般的火车头领着,弯进玩具一般精致讲究的乡间,再绕过玩具一般完美的大水塔,如茵的绿地则在四面围绕。工厂前方有几座喷着水的喷泉,数条壮阔的林荫大道上,熠熠生辉的豪华马车络绎不绝。那些都是拉风的维多利亚马车,而拉车的马弓着颈子腾跃着,驭马的车夫头戴高帽,车上的窈窕淑女则打着阳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