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雷夫人1877年随丈夫广州沙面堂牧师格雷从英国来到广州,在广州居住的14个月期间,格雷夫人坚持写信描述她在广州的见闻和感想,给家乡的妈妈和其他有兴趣的亲友传阅。这种带有游记性质的信她一共写了44封,回英国后于1880年,取名为《在广州的十四个月》(Fourteen Months in Canton),增加了一篇自序,结集出版。翻译出版时名为《广州来信》。
格雷夫人跟着丈夫游广州,不单看名胜古迹,而且走街串巷,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她不但以文字记录,而且绘制了一幅幅有趣的图画,为我们留下了19世纪末广州社会生活的活泼直观的可贵记录。
《广州来信》是《遗落在西方的广州记忆》丛书之一。
《遗落在西方的广州记忆》丛书简介
广州曾是除澳门外西方人wy可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承担着外交、外贸等管理职责。可以说,以广州代表中国,在西方曾经是很普遍的现象。
作为中国对外交往门户的广州,历史上接待过无数的西方人,其中有画家、商人、学者、传教士、外交官,也有来自底层的水手、工人等。他们在广州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很多人甚至较深地融入了中国式的生活。他们以好奇的眼光欣赏广州,以独特的视角记载广州的风光、地理、人文等。虽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中国历史传统的博大,这些记载也难免有变形、疏漏的一面。他们实际上塑造和建构的是一个他们眼中的广州,映射到了西方读者的头脑中,逐渐构成了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
近代中国天翻地覆,当年广州的山川风物和社会百态多已烟消云散,却被凝固在这些西方人的著述当中了,就像琥珀中的昆虫,历尽岁月,依然栩栩如生。现在的我们可以借此大致清晰直观地看清近代广州甚至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它们不但是研究中外关系和文化互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即便是一般百姓,也可据以追怀老广州的街坊店铺、寺庙宫观、五行八作、花艇疍家,甚至琶洲砥柱、大通烟雨。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遗落在西方的广州记忆,可以重温历史上作为中国对外交往门户的广州之风采,发扬其中的和平、对话、交流、发展等人类共同智慧和人文精神,摒弃曾经的愚昧、自大、保守、落后等鄙陋,在新的时代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这本小书是由我在广州居住的14个月内写给亲友的 信件构成的。我在那里有很多机会目睹中国人的私密生活。谨以本书献给我的丈夫约翰·亨利·格雷,他长期在广州居住,跟当地人亲密交往,使我得以目睹和了解后者的礼仪和习俗。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家,这里是沙面小岛的尽头,几乎完全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有非常宽阔的视野,可以欣赏美丽的珠江。
一个保姆拿了一块小布丁放到手心里,把它揉碎,再喂到女主人的嘴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吃水果的时候。中国太太一切都依赖保姆,自己什么都不动手。中国太太无法理解我们欧洲女士;她们说:“你们都跟男人一样啊。”
中国女人夏天有固定的一套装扮,冬天、秋天和春天也各有一套。在中国,没有任何服装店被要求引领时尚;一种新款会被中国女人怀疑和厌恶。习俗也以简朴为贵。
原来我们第一天吃的是狗肉,第二天上桌的是猫肉,第三天早上吃的则是鼠肉。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我被事先告知那些碟子里面放的是什么,我半口也吃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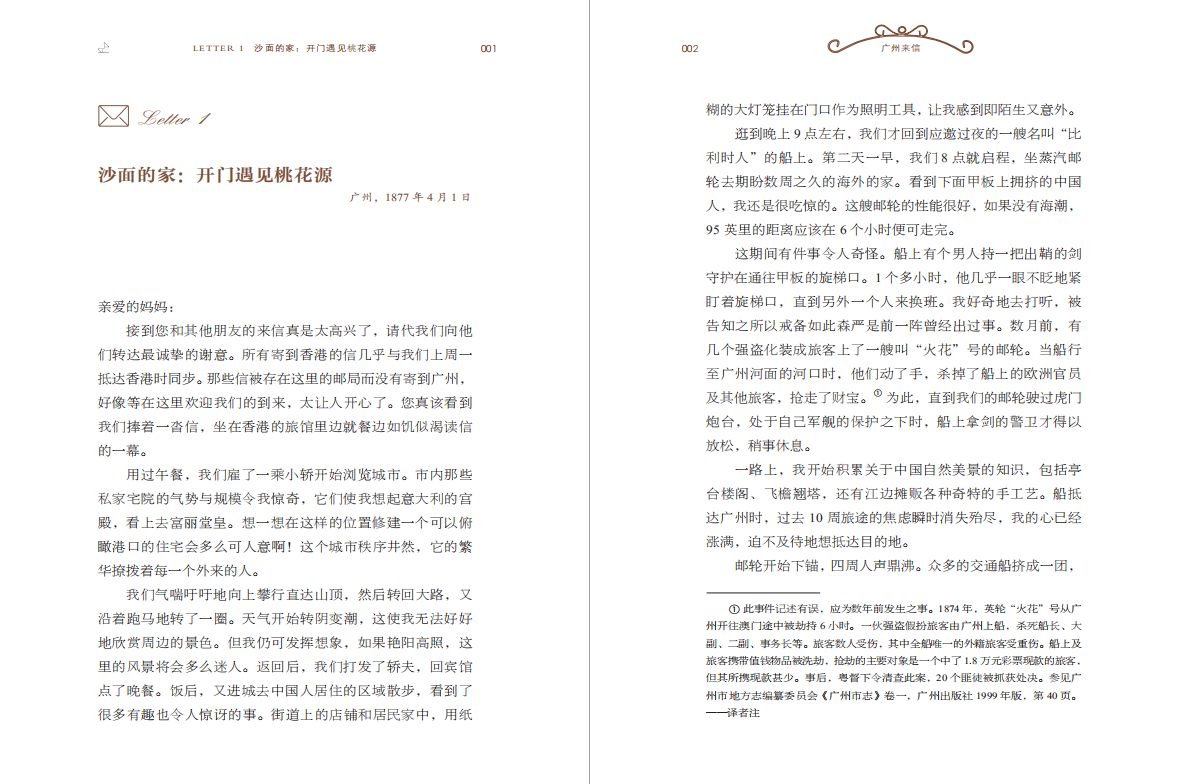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