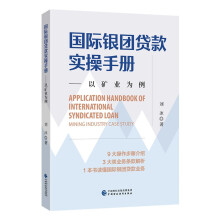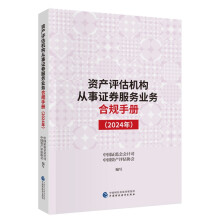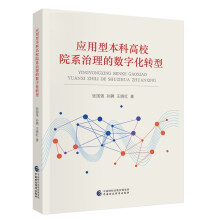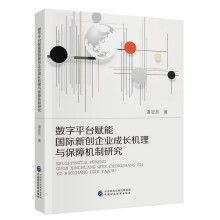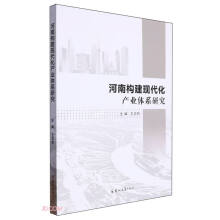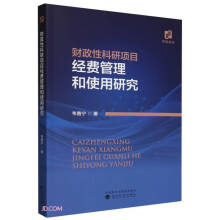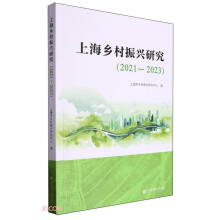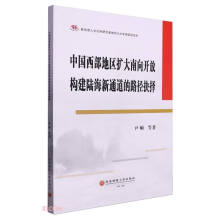《经济所人记忆(第1辑)》:
我与孟和先生素不相识,1929年年底,经老友樊弘同志的介绍,参加了社会调查所。当时该所位于北平南长街东河沿6号,除孟和先生外,研究人员中有樊弘、王子建、杨西孟等,都是早在社会调查部时代就已进所的。另有吴半农、曾炳钧、刘心铨、韩德章等,都是1929年改为社会调查所后进所的,时间比我略早。研究人员总数不过十几人。做辅助工作的首推计算员,他们的职责是将调查研究所得数据按照研究人员的设计和程式进行计算,以利于统计和分析。当时可用的计算工具只有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后来有了电动计算机,就算是新式利器了,与50年后的今天相比,计算效率当然很差,为此,计算员人数较多,与研究人员约略相等。此外,图书馆员有2人,他们的工作也是重要的辅助环节。至于事务人员,只有会计1人,庶务1人,全所除研究工作外,其他一切事务都由这两位办理。事务人员在全所总人数中所占比例极小,这在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不曾改变。
社会调查所初期的调查研究工作大部分是社会调查部工作的继续,包括城市和农村社会调查以及劳工问题、人口问题的研究等。例如,我于1930年与林颂河、邢必信、张铁铮三位合编的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便是以前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的续编。又如我所写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部2330个案的分析》,便是此前高君哲调查所得结果的分析整理。前一课题属于劳工问题,后一课题则属于城市社会调查。
城市社会调查中应予特别提及的,是北平市工人生活调查,以及以后据以按期编制的北平工人生活费指数。这项工作在当时实属创举,指数的编制持续多年,影响所及,上海市社会局和天津南开大学先后在所在地区从事类似的调查研究和编制指数,对于了解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提供了客观事实和统计数字。30年代,北平协和医院每月发放职工生活津贴的金额,即以社会调查所编制的上述指数为根据,说明这项指数在当时即已有实用价值,尽管由于风气未开,实用未能普遍。其后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被派在赣南钨矿区工作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每月调整钨砂收购价缺乏科学根据,畸轻畸重,经常引起矿工不满。我乃约同张铁铮,组织人力,在赣南各大钨矿区进行了一次钨砂生产成本调查,以后并逐月据以编制各矿区生产成本楷数,以供当局制定收购价时参考。这些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它叉说明社会调查所倡导的这项社会调查工作,尽管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其效不彰,但是源远流长,只要遇到适宜的土壤,就能收到相应的积极效果。
社会调查所的工作在孟和先生的苦心擘画和惨淡经营之下,自无到有,自简趋繁,数年之间,发展很快。当时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除极少数外,都是30岁以下的有志于学问的青年。他们在孟和先生的激励和指导之下,各选专题,奋力探究;同事之间则互相切磋,协作无间。其中,许多人并能锲而不舍,以后成了知名学者,有的到了今天虽已白发苍苍,还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孜孜不倦地工作。这种情况与孟和先生的个人品德和在早年即已树立的学风是分不开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