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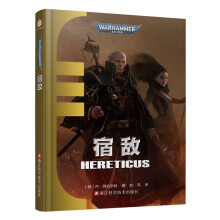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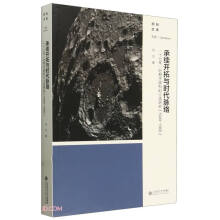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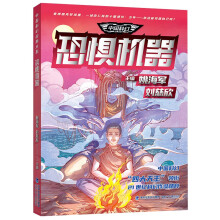
在纽约长岛,在不可预测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小男孩悲叹着夏天即将结束,六年级即将到来。父亲忙于工作、母亲成天酗酒。他和兄弟吉姆在简陋的地下室里用纸板搭起了一座以社区为原型的“白石镇”,甚至做了朋友和邻居的泥人塑像。
但随后发生的事件给孩子们的夜间游戏增添了阴暗的色彩:失踪、死亡和幽灵目击,一个阴险的男人在天黑后开着白车在附近徘徊……奇怪的是,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似乎都直接对应着妹妹玛丽对地下室微型小镇的改变。
第二天早上刚刚能勉强通行,管道工就来我家修好了供暖用的燃油炉。能离开厨房真是让人舒爽。吉姆看起来好多了,尽管他还是感着冒。外头寒风依旧,不过太阳出来了。吉姆和我出门帮爸爸铲雪,我们挖出了一条通往马路,还能开车的道,否则爸爸晚上没法上班。我等着机会跟吉姆搭话,后来爸爸总算暂时走进了房子。
“我在巴尔齐塔的事上错了,”我说,“但我知道那个开白车的人住哪了。”
“哪儿?”
我跟他说了那栋建在树林边、带了车库的房子。
“是不是他杀了巴尔齐塔,把尸体抛在路边等着雪把他埋了?”
“我不这么想。”我说,“我只是觉得自己错了。”
“既然你不这么认为,那就先不管这事。”吉姆说,“我们要去趟树林,你得把那人的房子指给我看。不过,我们必须等到雪化,不然那人会沿着脚印追到我们家的。”
“我已经留下脚印了。”
“但愿雪及时掩埋了它们。”
圣诞节假期剩下没几天的时候,我和吉姆滑着雪橇参加了好多小孩都在打的大雪仗。结束后,我们在边上的海湾上走了一圈。拉里·马奇跟我们说,他爸讲这片湾区已经冻上了。吉姆说马奇爸爸的脑袋才被冻上了,但我们走上海湾,发现他所言不虚。阳光下,鹅毛般的大雪在我们身边飘舞,脚下海水结成的冰少说厚一英尺。这些海冰有的地方起伏不平,有的地方光滑如镜,你能透过它看到底下的黑暗。要不是我怕落水,吉姆可能已经自顾自地走到凯普翠岛上去了。我告诉他我不继续朝前,而是要回岸上时,他转身看着我,说:“我知道玛丽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了。”
“为啥?”我问她。
“爷爷最近没在赛马了。他前两天告诉我,他在等着海厄利亚的比赛。我敢说,玛丽觉得自己也得和爷爷一样,得度个假期。”
那天晚上在破镇前,我们问了玛丽吉姆的想法对不对。她没说什么,而是走到板子前研究了一通。我们俩站在一旁等了段时间,后来吉姆看着我摇摇头。他绕过玛丽,递给她那个代表贼的玩具。玛丽推开了他的胳膊。
“不。”她扫视着板子,找到了那辆停在巴尔齐塔家门口的白色汽车。她拿起车子,放在我们家门前。
“什么时候?”吉姆问。
“现在。”玛丽说。
“现在?”我问。
“就是现在。”玛丽回答。
吉姆三步并作两步窜上楼梯,我紧跟在他身后。我们扒着前窗,望着外面的夜。满月之下,大雪纷飞。“我操。”吉姆骂了一声。一秒过后,我看到了汽车的车灯。那辆白色的汽车慢慢地爬过了我们家的门。等到它尾灯消失,吉姆才站起身坐到沙发上。
“我跟你说过了。”我说。
我们返回地下室,告诉玛丽她说得没错。她这时已经返回楼梯自己那一旁,变成了米奇,哈克马老师还称赞他所有题都答对了。吉姆把他的注意力放回了破镇。“徘徊者在徘徊。”他说。
“嗯?”我说。
“嘿,看。”吉姆说,“她改了位置。”他指着查理·爱迪生。那个泥人现在躺在我们院子里。
“这什么意思?”我感到恐惧扼住了我的咽喉。
“他沿着排水管,找上门来了。”吉姆说。
我干笑了几声。但等到熄了灯躺在床上,我感到查理就在打开的衣橱门后面,那时候我可就一点也笑不出来了。那个晚上,查理通过天线说话了。我至少三次在嘎吱声里听到了他在呼喊他的妈妈,而且每次都是在我刚刚有那么点睡意的时候。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