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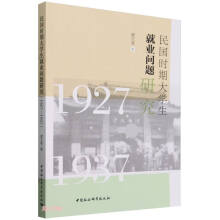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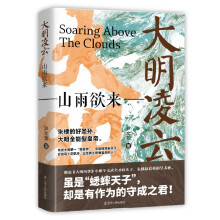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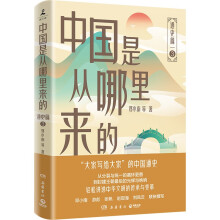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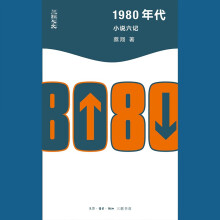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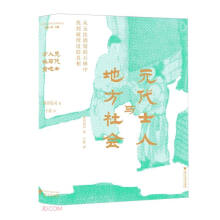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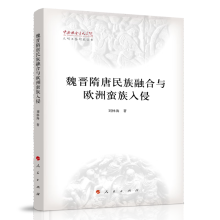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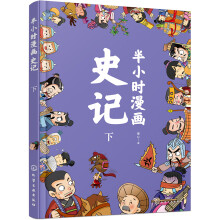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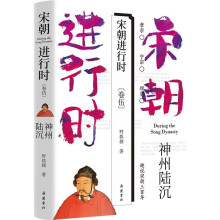
◎完整呈现引人深思的金国衰亡史,细节还原惊心动魄的城池攻防战。
◎面对内忧外患,金国统治者作出哪些决策,导致国家从国运巅峰猛然跌落并迅速灭亡?
◎1232年汴京疫病爆发如何影响金国命运?
◎围攻大型城池为何堪称古代的“高科技”战争?
◎对于决策者:
体会决策失误是怎样导致个人、组织陷入危机的,思考如何避免作出错误抉择。
◎对于历史迷:
了解金朝盛极一时但迅速衰亡的过程,从中洞悉历史上众多强权的兴衰之道。
◎对于军事迷:
从蒙古骑兵与金国武士的交锋,感受古代城池攻防战中勇气、智慧与技艺的对决。
12世纪,发祥于东北一隅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大金王朝,一度跃居东亚霸主地位。这个政权在极短时间内灭亡辽国,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使北宋蒙受“靖康之耻”。然而自1211年蒙古军队南下侵袭开始,二十多年间,金国接连丧师失地,抵抗运动中心被迫从中都先后迁到汴京、蔡州,最终在蒙古和南宋军队的夹攻中覆亡。
本书以蒙金战争期间几场重要的“围城战”为主线,还原了几场关键大型战役中双方军事布局和交战历程,揭秘了金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变、兵变及权力更迭,展现了中都、汴京等城市被蒙古军围困期间,金国军民的抵御策略,以及物资短缺、疫病来袭情境中的挣扎求存及心理状态。作者以通俗晓畅的笔法完整呈现了金王朝从组织抵御、负隅顽抗到君死国亡的全过程,金朝的治乱兴衰之缘由寓于叙事之中。
外部面临新兴势力的冲击,境内自然灾害频繁,而统治集团权力斗争导致人祸不断,君主又缺乏力挽狂澜的雄才大略……种种因素使得金国国势日益窘困,最终堕入绝境。金朝的亡国史有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游牧民与城墙
这道防线,仅仅是金朝裹在最外面的一层重铠。一旦游牧骑兵突破了遮护国境的界壕和边堡,想再进一步,还有另一番景象等着他。
同界壕一样,内地的城池也多采用夯土版筑,也就是筑土城,一般是正方形或者长方形。在中国南方,由于降雨偏多,土城容易塌陷,如果财力允许,会考虑用砖、灰包砌土城内外两壁。在北方,明代以前,砖包砌城很少见。有一次,金世宗想给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的城郭包上砖石,宰相劝他爱惜民力,只好作罢。当然,黄土夯筑的城墙一样坚固,若再采用赫连勃勃那样的“蒸土”法,甚至可以达到锥子都插不进的硬度。
土城倒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发展了上千年,到宋金时期已经相当成熟的军事工程学。
想象一下,一群漠北赶来的骑士,马鞍下垫的障泥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沙,黝黑的面庞犹带着边地厮杀溅上的血污,驻马怅望平原上矗立的那一座座伟岸城池。
距离城池老远,草原汉子当成心肝宝贝的战马,就会遇到各种危险的障碍器材:带尖刺的铁蒺藜、满布铁钉的地涩,等于现代的“布雷区”,还有截断道路的拒马枪、绊马索、鹿砦,等等。
再走近一点,骑士大概会遇到一条环绕城墙的护城河,或无水的壕。护城河是一条面阔、底窄的人工河,通常阔二丈以上,深一丈,上面只有一道狭窄的吊桥,通过绞车升降。换句话说,骑士没法像在草原上那样,找个下游的浅滩便涉水而渡。河、壕的底部,可能设有削尖的木刺或其他杀人装置。在护城河外围,是威力巨大的床子弩或抛石机(砲)的杀戮地带。
如果骑士平安越过护城河,便可近距离感受一下眼前这座庞然大物。
稍具规模的城池,城墙高大宽厚,而且越往下越厚,四角筑有供瞭望和射击的角楼。城墙顶端有一圈面向外侧的雉堞,高约二米,开有射孔,每隔数尺还开一个垛口,让雉堞看起来呈锯齿状,绵密相续。守城士兵藏身雉堞之后,通过射孔或垛口狙击城外之敌。垛口内外,敷设篱笆、木桩、土囊、布幔、绳网一类的护具,缓冲城外射入的矢石,甚至有一些应急用的“移动碉堡”,如行城、杂楼,为守军提供防护。夜幕降临后,铁链吊着大火炬,从雉堞后垂下,照亮城墙外的一圈警戒地带,防备夜袭。
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筑有凸出于墙体的一种碉堡,下宽上窄,就是前面说的“马面”。马面上也有雉堞或战棚,瞰制城脚,与角楼、垛口呼应,形成无死角的交叉火力。宋元时期很多城池的马面修筑得非常密集,远远望去如同由长墙连锁起来的一座座高塔,煞是壮观。
城墙的最薄弱处,是容易被撞开或者叛徒偷偷打开的城门。城门通常有吊门做双重保险。城门上,筑有单檐或重檐的城楼,城门外侧,加筑半圆形或矩形的狭小外堡“瓮城”,堪称全方位立体掩护。瓮城的小门开在一侧或两侧,不会正对城门,所以,从瓮城到城门,要曲折出入。
距离城门五十到一百米远,在护城河内侧,有时还筑有一道低矮的挡墙,大概一人多高,也开有射孔,叫作羊马墙,进一步掩护主城。除了一层叠一层的各类城墙,为了抵御北骑冲突,金朝军队还在城门内外构筑过一种“迷魂墙”,也称“八卦墙”。顾名思义,应该是一种曲折往复的迷宫式屏障。
在这每一项防御工事后面,都集结了武装到牙齿的守城士兵,向一切来犯者倾泻密集的弩箭、石砲、滚木礌石(石头或布满铁钉的木头柱子,通过绞车投放)、烧得滚沸的油和粪便,还有杀伤力强大的初级火器——火球、火药箭和飞火枪。
骑士站在护城河边上,昂起头,可以依稀辨认出城上守军那一张张愤怒而恐惧的面孔。在他们之间,是一段难以跨越、分判生死的距离,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地带”。
粗悍的游牧民心里大概有点发怵。最符合骑士美学的线条是纵横驰突的直线,而城池设计的美学,乃是折线和曲线。在这里,步步惊心,处处杀机,所有空间仿佛都被处心积虑地设计成不利于他和他的战马。
骑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穿过羊马墙和迷魂墙,闯进瓮城,才发现这其实是个伪装的城门,要拐个弯才能看到正门。冲入正门,也许还有一个坑煞人的内瓮城,这个地方狭窄得要命,马掉个头都很困难。
待骑士历尽艰险,终于从正门冲入城内,也休想纵马驰骋,从东头酣畅淋漓地杀到西头——中国城池普遍设计有大量的丁字街、死胡同,以便巷战……
这种“重铠全装”的坚城,别说游牧民了,对这套防御体系再熟悉不过的中原军队也常常望而却步。
《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攻城视为下下策:“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大盾牌)辒(攻城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中国史书描述攻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恐怕就是“蚁附”,形容城墙外侧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的士兵。也可见,在这种场合,人命同蝼蚁一样轻贱。
美国汉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想到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世纪以来西欧发展出了轰塌城墙的火炮,而中国的火器仍然是以杀伤人员为主?他的答案居然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城墙太厚,与西欧城堡完全不在同一级别上。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幕墙厚度绝少超过十米。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任何火炮也轰不开十多米厚的中国城墙。
虽然没有火炮,但为了对付这套城池防御体系,古代至中世纪的中西方战术,基本都是三板斧及其不同组合:翻越城墙,径直穿透城墙,挖掘地下坑道。一旦这三板斧都不管用,就只好靠长期围困饿死渴死守军。为了方便运用这三条策略,中国古人发明了许多攻城器械和方法,什么巢车、望楼车、壕桥、尖头木驴、木幔车、钩撞车、搭车、杷车、云梯、飞梯,各种型号的抛石机和弩箭,还有土山、地道,等等。其中好些自先秦以来一直沿用,也有一些属于新发明或改进品。不过,对这些凝聚了几千年古老智慧的军用技术,即将来到城墙脚下的游牧民,暂时还叫不出名字。
楔子 一段“崖山”之前的故事 01
上 篇
第一章 危 机 003
一、射弓宴 003
二、“用夏变夷” 007
三、北方来的强敌 013
第二章 防 秋 019
一、以一敌百 019
二、女真长城 023
三、游牧民与城墙 028
第三章 焦 土 033
一、哀兵必胜 033
二、世界第一野战军 039
三、骑兵也能攻城? 042
第四章 敌 袭 046
一、“护国坛被焚!” 046
二、扼胡岭,难扼胡 050
三、范成大的诅咒 056
四、边风急兮城上寒 065
第五章 惊 变 071
一、卫绍王画像 071
二、通玄门之变 075
三、巨人卫队死战 081
四、从彰德来的人 086
五、宣宗当国 090
第六章 抉 择 096
一、幽闭恐惧 096
二、1214年“南逃”大讨论 102
三、中都陷落 110
四、命运的歧路 120
下 篇
第七章 孤 注 135
一、中兴的希望 135
二、“好男子,来世当生我家!” 142
三、河中绞肉机 151
四、“内线优势”VS“斡腹” 164
第八章 三 峰 175
一、“存与亡,有天命!” 175
二、大雪满弓刀 183
三、烽火照南京 190
第九章 困 兽 197
一、帝国的攻城术 197
二、开兴围城 204
三、巨石砲与飞火枪 212
四、灰、黑二骑士 221
第十章 人 心 233
一、河畔的远征 233
二、人生似巢燕 245
三、崔立:一日君王 254
四、郑王碑下“罗生门” 269
插曲:刺崔 278
第十一章 覆 巢 284
一、照碧堂 284
二、防御专家仲德 296
三、宋军报到! 308
四、攻城竞赛 321
五、幽兰轩的烈火 333
尾声:又见黄河渡 343
参考文献 351
后 记 363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生动而真实,宏大又精细,一部兼具军事史、政治史和文化史品质的好书,不仅再现13世纪的烽火刀兵,也给出了层次丰富的历史解释。细节描摹都有史料支撑,堪比专业论著,对历史人物个体命运的关注则感情深蕴,不输文学作品。佳作难得,欢喜推荐。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书展现了一个王朝拼命挣扎直至覆亡的过程,更写出了时代巨变之下千万人的悲惨命运。
——张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书描绘了铁与火、血与泪的战争画卷。
——党宝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围绕城池而展开的最残酷的几次较量之一,北方骑在马上的人,被北方以北的骑马人践踏,用血肉和砖石垒砌的,又被鲜血和钢铁摧垮。汝之捷报,彼之噩耗,历史大潮,终不改道。
——刘鹤(军事历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