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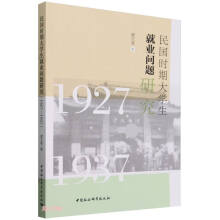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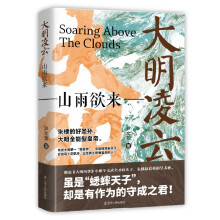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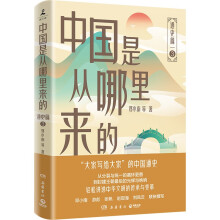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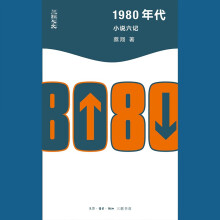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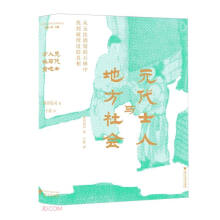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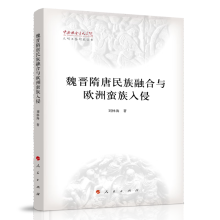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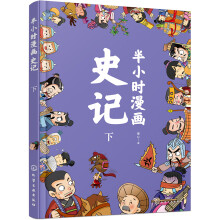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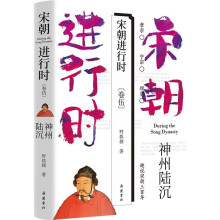
不因个人好恶写历史,重视历史背后的因果关系,为历史正本清源。
本书贯穿黄仁宇 “大历史”观,集合了其历年来的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对其所有著作中的观点进行补充,并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加以解说,可称得上是其著作的精华解释。目的仍在于从各种历史故事中探求中国历次改革的得失及今后的出路。此次出版的《黄仁宇全集》大字本系列, 是在本社2012年出版的全集精装版基础上再行校订,为大十六开本、大字号的设计风格,提高了阅读舒适度。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故事:周立禺中学刚毕业时值对外留学开放尺度,他的父母立即措资使他到美国上大学。初时他不肯去,因为当时他热恋同班的张惜音,果然,他还在爱荷华州忙大考的时候她已和人订婚;等他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她已结婚。而周立禺仍是孑然一身,而且美国学位也没有当初想象的有用。五年之后,立禺想起当日父母催逼自己勉从的一段经过,不能无介于怀。
他又再度游欧,十年之后自己的婚姻事业也有了成就,张惜音则在离婚之后酗酒。立禺再看到她的时候前后已判若两人,他就难于想象自己当初何以会爱上她……再隔五年十年旧梦重温必更有不同的看法,往事本身的基数未变,他和她对过去之观感则因以后的发展而转移。
在某些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周立禺或张惜音。我们也都是各人未出版之自传的作家,也经常对我们心目中之自传经年累月地不断修改,修改起来的时候,不仅前后措辞不同,即取材也有很大的差别,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个人经历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遭遇和发展亦然。这种说法对1990年代的中国人用意长远,因为过去的七十年,中国已经历过一段跨时代的大改革。1920年间中国面临一个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局面(南北即有广州与北京两政府),今日则有似于隋唐之勃兴,过去需要三百多年的动乱作背景,在20世纪只花了七十年渡过此难关,不止此也,中国之历史现已与西洋文化汇合。
“你真有把握确是如此?”你可能这样问我。
用不着问我。你只要反躬自问:你的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家中生活习惯、婚姻关系、所受的教育、所承担的工作和所创造的事业是不是与1920年代你父祖所经历的全然不同?这不可能全然由于你个人之选择,而是侧后的社会背景已经过一段改造、遭遇到一段大变动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已有了一番整体之调整。从大陆一次迁徙到台湾的人户即二百万,早岁金门御敌,今日大陆观光。过去七十年有了乾坤颠倒山河变色的经验,今日海峡两岸尽力通商,都希望在商业条例之中,坚定了管理新社会之原则。
这时候如不修改历史何时修改?
一百五十多年前有鸦片战争,兹后外强在中国保持着领事裁判权,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仍是几百万农村组成的大集团,本身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因对外贸易带来的繁荣,也只限于通商口岸,很难在租界之外发展,今日则已脱离这局面。抗战刚开始,胡适即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要慎重将事,这些情形都能和今日局面对照解释得前后连贯。又不止此也,如果我们把秦汉当做“第一帝国”,隋唐宋当做“第二帝国”,明清当做“第三帝国”,各以其财政税收作行政之张本,则全部经历与今日对照,也可以将当中大变动解释得明白。我们更将英国与荷兰在16、17世纪,经过变乱从农业体制进入商业体制的情形,与今日中国比较,也能说得互相衔接。在今日台湾与大陆提议邦联或联邦制的时候,则四百年前荷兰的例子更可供借镜。
将此中宏观情貌写为历史,则为“大历史”。
这大历史不可能与传统之中国通史同一篇幅或结构。主要因为今日中国之社会不论在大陆或台湾,均与传统中国社会(即胡适所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有了至远之距离。在改造过程中,前有八年抗战,中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之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军令下与强敌作八年生死战,此已为洪荒以来之所未有,而接着又展开约四年之内战,更在世界史里难于找到类似例子。这突出发展,即不可能被传统之篇幅容纳,抚今追昔,我们一定也会将王安石变法、清朝入关等事迹解释得与以前不同。前面已经说过: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中国大历史》中文本于1993年10月在台北出版。首先编辑先生即已慎重将事,在封颜之背面说明这书“虽然是通史性的论著,却突破了传统通史的格局”。可是所遇到的书评,仍大部分以脱离传统规范相指责。
王汎森先生在《中国时报》“开卷”的书评,出于善意。他说:“(此书)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字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他又指出我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叙述”。
这都不失为持平的批评,我既认为中国历史至此已与西洋文化汇合,则从外看来与从内看去已无不能调和之差异(我只希望人人如此,至今还有很多外国人以为我之“大历史”过于中国本位),缘于前述中国人之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都已经过西洋文化之冲击而作全面目之调整,王先生自己的文字即已表示着高度的外文之影响,如“作者似乎过度强调财税等物质的因素,而忽略文化层面的历史作用”,非熟练于西欧文字者不能随意写出。
可是我的辩论也源于这温和的批评。我们今日所谓“经济” (economics)的束缚,本身即是文化层次的产物。既以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每一朝代在创制的阶段即已充分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哲学及宇宙观。明朝的赋役更强烈地表现了明太祖的复古思想,这可以从他所颁“大诰”及在户部迭次训话时看出(注意梁方仲认为明代虽在后期行一条鞭法,其范畴不出于“洪武型”)。 六百年后我们将这题材视之为一个技术问题,当初朱元璋提倡“藏富于民”指斥桑弘羊与王安石,却已将赋役视为道德问题。
《中国大历史》既已将题材高度压缩,又以问题作重心,即不能如传统的通史,将哲学、美术、经济各分一栏论列,本来这些区隔无非是学院分工的办法,与历史成综合性的发展本身不同。在以归纳法为主旨的眼光看来,我并未忽视文化层面的重要,儒家之“克己复礼”,我以通俗文字“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之团结和仪礼上之周到等等”在书中提到八次,提及孟子也有九次,而且此书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卷,以康德所述“事物自身”参入结论,当中提及杨朱、墨翟、董仲舒的宇宙观(未具名)、张衡、王充、玄奘、苏绰的根据周礼立制、宋朝之理学、清初之“实用主义”等等,也不能算是忽略文化层面的历史作用了。至于每一题材只能用一两句综述,则因全部资料业已高度压缩,并已在实用的场合中论及。
况且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提及文化层次,也不能限于传统的经典著作,我书中更叙述秦俑、汉瓦、敦煌石窟、《清明上河图》和《白蛇传》,则因不常见,较诸书为详。
至于龚鹏程教授在《中央日报》的评论,则可算作恶意的抨击,他除了全面否定《中国大历史》的立场外,并且对作者作个人指向(adhominem)的否定。他说及我在研究明代财政的“成果”外,立即说起:“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再说:“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之常识所惊。”我以九十三个字来谈明代思想,“而且几乎全错”,既然如此,那他又何苦操劳写下这长篇大论的文字,又提及书中细节,并且预言“我不相信黄先生能妥善回答”?他的结论,要我“悬崖勒马”,用词似民国初年军阀之通电。
本来这样所谓“书评”毋庸作答,你讨厌我,我鄙视你,写来辩去,必成“骂街式”的文人相轻。只是在龚教授全面否定之余,我却不作答也要向我的读者解释。
《中国大历史》中文版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也受“开卷”十六人书评小组列入推荐书榜,英文版则早已经若干美国大学采用为教科书,也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海内外人员之参考。今年(1994年)夏天香港行政局一位议员即亲买一本赠港督彭定康,请他注意书中所叙。此书也经香港电视介绍,大陆方面除了《读书》已在第八期转载此书之第二十章外,已准备在北京出简体字版,日文版则经东京的东方书店筹措,预定在今年4月出书。此中必有无数为《大历史》奔走的朋友,以下是对他们的交代。至于书评内所述“只是由于他根本无力处理历史中非技术的部分”,则无法分辩,只有至必要时可将此文附刊于《大历史》各再版之后,同时读者也可参考我所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的“道学家”。《万历十五年》内《李贽》一章已综合我对明代思想史的看法,即将出版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更有提及王阳明之处。
◎书评说《大历史》提及今日汉字为数二万,“他不晓得康熙字典上所收即有四万九千字吗?”
中国字数至今缺乏具有科学性之统计。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提及:“今日中文在最大之字典有字远逾四万。但是归结起来约七千铅字构成报纸之所需,其中约三千为通过识字的标准。”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教授(Derk Bodde)可算得今日西方最大汉学家之一,他在《中国思想、社会及科学》(Chinese Thought,Society,and Science)则述及:“……在现代未经节录之字典有字几至五万。但是这种字典所列很多字体已经过时,不常用,限于技术性,或者属于标准字之变体。”
抗战前所出之《辞源》有单字约一万零九百五十。大陆刊行之《新华字典》可能为最畅销之字典,有字约一万二千。《马氏汉英字典》 (Mathrows’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有字七千七百八十五(很多科技名词尤以化学名词原出自西文)。
我所谓二万,根据战前之估计,包括以上各字典辞典所未列之字,如恭亲王奕之,与康熙之名玄烨之烨,现在看来此估计似过高,以后修订可能近于一万五六千。
我希望研究语言文字之专家利用电脑将现行字作一统计,我猜测必低于二万,不可能多至四万余。要我接受《康熙字典》之字数,即是将我写历史向后修订。
◎书评说我曾说“五行金、木、水、火、土为万物相配置的方法,其根源出自《易经》 ”。“ 《易经》恰巧也不曾谈及五行”,所以我应当“翻一翻这本书”。
《大历史》有关此中关系之原文为:
他(汉武帝)朝中博士(董仲舒)认为五行(木、火、土、金、水)和东西南北中之五方、五种基本之色彩、五声之音阶、五种个人之德性,甚至五项施政之功能都互相配合而融会贯通。例如火,色赤,见于夏季,与用兵有关。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为人世间任何“物”,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间的一种关系或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相关价值,所以可以用数学方法操纵之,其根源出于《易经》,它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古老经典。(页五十二至五十三)
以上所说确定地指出其观念及信仰来自《易经》。至于《易经》与五行的关系,读者可以参考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内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我生平只用过《康熙字典》一次,也只“翻一翻”《易经》一次,此因研究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时,发现他曾著《儿易》一书。我曾怀疑此中有特殊之数学思想,结果大失所望。我对一般读者的劝告即是接受李约瑟博士对《易经》的评价,这是一只“档案箱”(File Cabin),若不如此只有自己研钻作《易经》专家,我再提醒读者,仅明朝人士所作对《易经》的解释与图说,已有二百二十部,内容彼此不同。
◎书评说商朝万物有灵的观念自周而中断,代之为周代对祖先的崇拜,这是谬说。“商人何尝没有祖先崇拜?周人何尝无万物有灵之信念,黄先生对有关宗教的问题太陌生了。”
这又是断章取义的恶意攻击。我原书所述为:
两个民族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页十六)
很显然,以上所述为源于国家之教义(Out of State),有组织,有全面性,与偶然的宗教意识或单独的宗教行为无关。简概言之,古人说“殷尚鬼”,表示着商朝的部落国家性格,尚未脱离巫教之操纵,亦仍逗留于神权时代。《史记》的《殷本纪》内提及帝武乙以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即表示人与神争的原始性格,此不可能见于周朝。
以周代商,宗教上有截前断后的改革。周朝所主持的祖先崇拜已与伦理观念及宗法社会不可区分,也是中国文化史里的特色之一。至于天子祭天,诸侯祭其封内山川,大夫祭其先,庶人无庙祭其寝,已不能视为animism。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亦即表示文教上的前后不同。孔子自己的宗教思想可以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再有樊迟问孝时他答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等文句看出。他又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终身仰慕周公,所以这一切文教之革新始自公元前12世纪,王权以礼乐作工具,祖先崇拜以孝为基础,这与商之尚鬼有了至远的距离。
我对宗教思想诚然陌生,所以在密歇根上学的时候曾往长老会、浸礼会路德教堂观察。可是我一直以为商周之间宗教性格的不同,是一种历史常识,至此被质问,被说“以想当然耳的态度,一刀割断商周”,至为惊讶。
◎书评说“秦以水德王,继周而兴,以黑色象征水正是该时代流行之思潮,何超时代之有?”
《史记》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这成为以后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之始。以前有人提及商代曾有类似更革,出于传说,秦始皇却自身作主如是之除旧布新。《汉书·郊祀志》即称“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可见得是首创。又不止此也,秦始皇改称黄河为“德水”,他在碣石所镌碑有“隳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字样。所以他以水象征秦代的统治,并及于封内不设防(这也对以后中国历史有长远之影响)。春秋战国期间诸侯常以河防为作战之工具,并以决堤危害邻国,始皇之统一免除了这一切纠纷,所以以水德色黑,有超过当时假科学的意义,也表示思想与行动互为表里。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仍是小问题。写《中国大历史》这样的书可能全无差错?只有外行才会有如此武断式的信念,那又何苦为这些题目斤斤计较?
这也是由于书评者的用心。他找到很多一般读者无从查考在黑白之间的争点,积少成多,使他们对作者的能力、眼光怀疑,“黄先生的史学与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这类踳谬太多了”。
于是我说《孟子》一书有天候地理的因素在,为“此妙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王阳明学说不是将佛家顿悟说植入儒家体系,亦无借重自然之趋向,更不涉及重视纪律之问题”,而且认为我既说中国受地理上之影响未曾在历史上产生资本主义,则应当“迁土弃地”。又以为我欢迎“台湾香港以及大陆改革开放的现象,对中国将资本主义化表示乐观”,是为自相矛盾,“却忽然忘却了他的地理决定论,真是太奇怪了”。
此人与我曾无交往,如何如此对我“太不恭敬”(他自己用语)?另一段他又说及我“对思想缺乏兴趣”(!)则好像“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看来则是无意之中我忽略了他的立场。他又提出他自己写通史的办法:“贵乎融摄综贯,而融贯史事须有一套观念,一套解释架构。”换言之需要唯心,以观念论先造成架构。
在我看来这是彻头彻尾地将中国史向后修订。《周礼》所谓“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只二十字已具在这样一套架构,如在中古时不仅可以倚之为写通史之指针,而且足以用之制造历史。可是这种体系需要所有政治、经济 (非现代之economy或economics,而系传统经国济世之术)全操在文人手中,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大前提下,用凭空构造(free construction)的方式将社会扭捏如理想。明初即已近乎这种做法。迄至利玛窦东来,犹叹赏治理中国者全系哲学家。我的《万历十五年》正是暴露此体制之弱点。
中国之士大夫阶级已因20世纪的革命永不复返,即以“知识分子”自成集团亦为日无多。最有力量左右国家政治、经济 (这倒是各大学经济系所注目之经济,因其有数目字之根据)的人物为银行家、实业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甚至广播员、新闻记者。军事家只在某种场合之下发挥其特长,大学教授聘为顾问多系专理外交之智囊,无一技之长(这才是技术)之文人仍欲如昔日官僚主义体制宰割一切不可得也。
我是否在提倡中国哲学无用论?
那亦不是我的着眼。最近我研究抗战期间的蒋介石,才领悟到王阳明之心学对他影响之大(也掺杂佛家顿悟说,也借重自然,也注意规律,全有文字作证)。而且他的日记里间常引用《诗经》与《书经》。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曾阅读过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很显然的,中国今后之文教有待于传统信念和习惯与眼前的新经济生活切磋琢磨而成,因之哲学与伦理仍具有领导的力量。但是新哲学家不能因袭于过去文人一手遮天的办法,以为文字均为其领域,对用其他学科为基点所作历史全不忍让。我个人即坚信任何历史学家无从否定今日中国由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进入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境界。因此之故,古籍专家参阅西方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只能有益无害。
抗战之前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他即将董仲舒到康有为之一段全长近两千年统称之为“经学时代”,书中云:“……在此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如以旧瓶装新酒焉。”他五十多年前写此段时即表示中国早已脱离此境界。王汎森先生论古史辨运动,也只反对“在倒洗澡盆时也把婴儿倒掉了”,并未反对洗澡。
今日去康有为又四分之三世纪,冯友兰也屡被整肃后身故。可是诸人梦想不到之事却已发生,即毛泽东不能想象之事都已发生。我自惭学浅术疏,但确认改制已成,毋庸托古。《周礼》系何人所作与我关系不深,可任专家争执。此书“间架性之设计”都成为了我研究财政税收之有力引导。况且《中国大历史》原为美国大学二年级学生读,在国内亦只希望为一般中学生、旅游者读,最多为大一学生参考,但仍遇到如是全面企图封杀,则除了本身防卫之外,不得不对当前历史教学发表意见。
其实今日之历史书籍只能由读者选择,不能由自命威权者所封杀,因为背景上,中国之改革,包含着各种群众运动。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事业等的改变,尤其脱离了过去“诗意之公平” (poem justic),已成为了每一个读者的人生体验,有如周立禺之于张惜音,不说自明,无待考证。我再摘录冯著《中国哲学史》里的一段:
中国哲学史只有一个,而写的中国哲学史则有日渐加多之势。然此人所写,彼以为非,彼之所写,复有人以为非,古之哲学家不可复生,究竟谁能定之?若究竟无人能定,则所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亦唯永远重写而已。
这也是我欢迎史学家将我书向前修订不要向后修订之主因。
不久之前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Samuel P·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事务》夏季号发表论文,题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内中提及过去国际间之冲突,出于君主间王室的冲突、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今后此类冲突升级,则为文明间之冲突,最显著之趋向则为西方文明在一边,“儒家与伊斯兰文明之结合”在另一边之越洋冲突。虽说亨教授结论之最后一句提及在适切之未来,宇宙一体之文明既不可得(此亦他个人意见),这项文明应在体验之中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存,但其文字则充满着备战之语调。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差距过大,所以西方国家裁减军备应有限度,并须在东亚及西南亚保持军备之优势,以防止儒教国家之扩充政策,并且设计利用各国家彼此间之冲突。西方国家则除了欧美应加紧联系之外,还要争取东欧及拉丁美洲,因为他们的“文化与西方接近”,日本为“西方之准会员”,所以要促进与它及与俄罗斯之联系。
亨廷顿也引用旁人之说,指出所谓儒教国家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国家内之华侨社团。以上各处互相具备新兴之工商业、金融中心、科技能力、服务性质之事业、良好之通讯网、广大的土地资源及劳动力,而以中国大陆作中心发展。冷战之后意识形态之敌意消失,各国以文化上共通之处促进经济之整体化。中国则不断地主持其扩张政策,在他看来,凡此都有向西方挑战之征象。
表面看来,亨廷顿不以种族、宗教、国家主义及经济之任何一面作“文化的冲突”之重点,而其实其文外之意即已集各色成见之大成。他既提及“西方文化”之核心地区,又有外围,尚有“准会员”如日本,又提及“西方文化事实上有许多方面渗入整个世界”,美国及其他西方势力利益则已在行动之中获得“普遍的合法性”,则与19世纪末期所谓“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有异曲同工之效用,总之即与罗斯福之所谓“四个自由”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在推崇中国为“四强之一”的着眼大相径庭,亦即将世界历史及美国历史向后修订。
亨廷顿将提倡“柔远人,来百工”之儒教文明,以及孟子所谓舜“东夷之人也”与文王“西夷之人也”的儒教之历史上的世界,与《可兰经》内三句五语不离“圣战”(Jihad)之传统相提并论,因其文明“非西方”则为反西方,既为反西方则须抑制,读来不仅令人觉得可怕,而又令人觉得滑稽。
这与我所谓历史教学何关?
中外人士近几十年来介绍儒家思想与文教传统,重分析而不重综合,将其细处论得莫测高深,其紧要之处与实用之处反又遗漏,历史教学又将1800年前后割为两段,讲得互不关联,因之发挥传统文教者则不究现局,研究现局者则不提文教传统。我们当对亨廷顿教授暴露此中关键感谢。《文明的冲突》一文仍主张西方应对其他文明之宗教哲学最基本的想法具深切之了解,并及于其人民因之对其利害之看法。借此句写在文之末端,而作者已对儒教及伊斯兰文明作有负面之判断。
《外交事务》夏季号之后,秋季有一文,题为“中国之兴起” (The Rise of China),作者克利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为前《纽约时报》之特派员,文称“中国非做坏事(之国家)亦非叛徒 (国家),但是他野心雄勃”。作者将今日中国比如本世纪初期之德国,因统一为民族国家后,借经济力量旺盛,有心经营远洋海军打破国际间之旧平衡也。克指出将来可能用兵之地一在南中国海,一在台湾海峡,另一可能在与日本争执之钓鱼岛。此文较切现实,亦更令人猛省。
如建立远洋海军则极难备而不用,打破国际间之旧平衡必为多数国家嫉妒,此又非道义上之问题,而为外交技术上之问题,想殷鉴重重,中国执政者必所深思,亦必能慎重将事。我只在此重复地提出《中国大历史》内之一段,注意此段因其文版,初与读者见面至今已逾五年。
虽说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极好机会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国家之间做和事佬,调节折冲,可是她也可能在两方之间同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国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挡人民共和国廉价而有技能之劳动力;而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之侵略性,这侵略性之趋向与中国文教传统无关。从一个以农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有侵略性的。
现在看来即有潜力打破国际间之旧平衡已被认为具侵略性,嫉视者应不只农业国家。如此更表现简明中国历史放大视界,不得不随时向前修订。传统的中国通史之作家无此顾虑也。
目 录
大历史不会萎缩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个人经验与历史
——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如何修订他的历史观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导 言
(一)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之由来
(二)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之大势所趋
(三)中国现代史之轮廓
(四)中学为用的缘由及应赋予的考虑
(五)“用”必须因“体”而调节
(六)结论
附:拟“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答客问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一)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
(二)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
(三)现代的展望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从珍珠港事变说起
历史传统与地理条件对近代改革运动的影响
——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
(一)改革步骤的三部曲
(二)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各国的改革模式
(三)中国的改革必须合乎国情
(四)回教国家的发展深受宗教的影响
1945年的上海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
资本主义与21世纪
(一)资本主义
(二)历史上之衍进
(三)因资本主义而产生之战时共产主义
(四)21世纪之展望
从历史的观点看东南亚金融危机
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的经验
掌握人类知识之全豹
道德与技术之间
附录 《大历史不会萎缩》编者说明
温馨提示:请使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