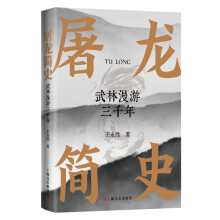“胡一刀,曲池,天枢!” “苗人凤,地仓,合谷!” 一个嘶哑的嗓子低沉地叫着。叫声中充满着怨毒和愤怒,语声从牙齿 缝中迸出来,似是千年万年、永恒的咒诅,每一个字音上涂着血和仇恨。 突突突突四声响,四道金光闪动,四枝金镖连珠发出,射向两块木牌 。 每块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绘着一个全身人形,一块上绘的是个浓髯粗豪 的大汉,旁注“胡一刀”三字;另一块上绘的是个瘦长汉子,旁注“苗人 凤”三字,人形上书明人体周身穴道。木牌下面接有一柄,两个身手矫捷 的壮汉各持一牌,在练武厅中满厅游走。 大厅东北角一张椅子中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白发婆婆,口中喊着胡一 刀或苗人凤穴道的名称。一个二十来岁的英俊少年劲装结束,镖囊中带着 十几枝金镖,听得那婆婆喊出穴道名称,右手一扬,就是一道金光射出, 钉向木牌。两个持牌壮汉头戴钢丝罩子,上身穿了厚棉袄再罩牛皮背心, 唯恐少年失了准头,金镖招呼到他们身上。两人窜高伏低,摇摆木牌,要 让他不易打中。 大厅外的窗口,伏着一个少女、一个青年汉子。两人在窗纸上挖破了 两个小孔,各用右眼凑着向里偷窥。两人见那少年身手不凡,发镖甚准, 不由得互相对望了一眼,脸上都露出讶异的神色。 天空黑沉沉的堆满了乌云。大雨倾盆而下,夹着一阵阵的电闪雷轰, 势道吓人。黄豆大的雨点打在地下,直溅到窗外两个少年男女的身上。 他们都身披油布雨衣,对厅上的事很感好奇,又再凑眼到窗洞上去看 时,只听得那婆婆说道:“准头还可将就,就是没劲儿,今日就练到这里 。”说着慢慢站起身来。 少女拉了那汉子一把,急忙转身,向外院走去。那汉子低声道:“这 是什么玩意见?”那少女道:“什么玩意儿?自然是练镖了。这人的准头 算是很不错的了。”那汉子道:“难道练镖我也不懂?可是木牌上干吗写 了什么胡一刀、苗人凤?”那少女道:“这就有点邪门。你不懂,我怎么 就懂了?咱们问爹爹去。” 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一张圆圆的鹅蛋脸,眼珠子黑漆漆的,两颊晕 红,周身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那汉子浓眉大眼,比那少女大着六七 岁,神情粗豪,脸上生满紫色小疮,相貌虽然有点丑陋,但步履轻健,精 神饱满,却也英气勃勃。 两人穿过院子,雨越下越大,泼得两人脸上都是水珠。少女取出手帕 抹去脸上水滴,红红白白的脸经水一洗,更是显得娇嫩。那汉子呆呆地望 着她,不由得呆了。少女侧过头来,故意歪了雨笠,让竹笠上的雨水都流 入了他衣领。那汉子看得出了神,竟自不觉。那少女噗哧一笑,轻轻叫了 声:“傻瓜!”走进花厅。 厅中东首生了好大一堆火,二十多个人团团围着,在火旁烘烤给雨淋 湿了的衣物。这群人身穿玄色或蓝色短衣,有的身上带着兵刃,是一群镖 客、趟子手和脚夫。厅上站着三个武官打扮的汉子。这三人刚进来避雨, 正在解去湿衣,斗然见到这明艳照人的少女,不由得眼睛都是一亮。 那少女走到烤火的人群中间,把一个精乾瘦削的老人拉在一旁,将适 才在后厅见到的事悄声说了。那老人约莫五十来岁,精神健旺,头上微见 花白,身高不过五尺,但目光炯炯,凛然有威。他听了那少女的话,眉头 一皱,低声呵责道:“又去惹事生非!若是让人家知觉了,岂不是自讨没 趣?”那少女伸伸舌头,笑道:“爹,这趟陪你老人家出来走镖,这可是 第十八回挨骂啦。”那老人道:“我教你练功夫时,旁人来偷瞧,那怎么 啦?” 那少女本来嬉皮笑脸,听父亲说了这句话,不禁心头一沉。她想起去 年有人悄悄在场外偷瞧她父亲演武,父亲明明知道,却不说破,在试发袖 箭之时,突然一箭,将那人打瞎了一只眼睛。总算他手下容情,劲道没使 足,否则袖箭穿脑而过,那里还有命在?父亲后来说,偷师窃艺,乃是武 林中的大忌,比偷窃财物更为人痛恨百倍。 那少女一想,倒有些后悔,适才不该偷看旁人练武,但姑娘的脾气要 强好胜,嘴上不肯服输,说道:“爹,那人的镖法也平常得紧,保管没人 偷学了。”老者脸一沉,斥道:“你这丫头,怎么开口就说旁人的玩意儿 不成?”那少女一笑,道:“谁叫我是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呢?” 三个武官烤火,不时斜眼瞟向那美貌少女,只是他父女俩话声很低, 听不到说些什么。那少女最后一句话说得大声了,一个武官听到“百胜神 拳马老镖头的女儿”几个字,瞧雎这短小瘦削、骨头没几两重的干瘪老头 ,又横着眼一扫插在厅口那枝黄底黑丝线绣着一匹插翅飞马的镖旗,鼻中 哼了一声,心想:“百胜神拳?吹得好大的气儿!” 原来这老者姓马,名行空,江湖上外号叫作“百胜神拳”。那少女是 他的独生爱女马春花。这名字透着有些儿俗气,可是江湖上的武人,也只 能给姑娘取个什么春啊花啊的名字。跟她一起偷看人家练镖的汉子姓徐, 单名一个铮字,是马行空的徒弟。 徐铮蹲在火堆旁烤火,见那武官不住用眼瞟着师妹,不由得心头有气 ,向他怒目瞪了一眼。那武官刚好回过头来,与他目光登时就对上了,心 想你这小子横眉怒目干么,也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徐铮本就是霹雳火 爆的脾气,眼见对方无礼,当下虎起了脸,目不转睛地瞪着那武官。 那武官约莫三十来岁,身高膀宽,一脸精悍之色。他哈哈一笑,向左 边的同伴道:“你瞧这小子斗鸡儿似的,是你偷了他婆娘还是怎地?”那 两个武官对着徐铮哈哈大笑。 徐铮大怒,霍地站起来,喝道:“你说什么?”那武官笑吟吟地道: “我说,小子唉,我说错啦,我跟你赔不是。”徐铮性子直,听到人家赔 不是,也就算了,正要坐下,那人笑道:“我知道人家不是偷了你婆娘, 准是偷了你妹子。” 徐铮一跃而起,便要扑上去动手,马行空喝道:“铮儿,坐下。”徐 铮一愕,脸孔胀得通红,道:“师父,你……你没听见?”马行空淡淡地 道:“人家官老爷们,爱说几句笑话儿,又干你什么事了?”徐铮对师父 的话向来半句不敢违拗,狠狠瞪着那个武官,却慢慢坐了下来。那三个武 官又是一阵大笑,更是肆无忌惮地瞧着马春花,目光中尽是淫邪之意。 马春花见这三人无礼,要待发作,却知爹爹素来不肯得罪官府,寻思 怎生想个法儿,跟这三个臭官儿打一场架。突然雷光一闪,照得满厅光亮 ,接着一个焦雷,震得各人耳朵嗡嗡发响,这霹雳便像是打在这厅上一般 。天上就似开了缺口,雨水大片大片地泼将下来。 雨声中只听得门口一人说道:“这雨实在大得很了,只得借光在宝庄 避一避。”庄上一名男仆说道:“厅上有火,大爷请进吧。” 厅门推开,进来了一男一女,男的长身玉立,气宇轩昂,背上负着一 个包裹,三十七八岁年纪。女的约莫二十二三岁,肤光胜雪,眉目如画, 竟是一个绝色丽人。马春花本来算得是个美女,但这丽人一到,立时就比 了下去。两人没穿雨衣,那少妇身上披着男子的外衣,已然全身尽湿。那 男子携着少妇的手,两人神态亲密,似是一对新婚夫妇。那男子找了一捆 麦杆,在地下铺平了,扶着少妇坐下,显得十分的温柔体贴。这二人衣饰 都很华贵,少妇头上插着一枝镶珠的黄金凤头钗,看那珍珠几有小指头大 小,光滑浑圆,甚是珍贵。马行空心中暗暗纳罕:“这一带道上甚不太平 ,强徒出没,这一对夫妇非富即贵为何不带一名侍从,两个儿孤孤单单地 赶道?”饶是他在江湖上混了一世,却也猜不透这二人的来路。 马春花见那少妇神情委顿,双目红肿,自是途中遇上大雨,十分辛苦 ,这般穿了湿衣烤火,湿气逼到体内,非生一场大病不可,当下打开衣箱 ,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走近去低声说道:“娘子,我这套粗布衣服,你 换一换,待你烘干衣衫,再换回吧。”那少妇好生感激,向她一笑,站起 身来,目光中似乎在向丈夫询问。那男子点点头,也向马春花一笑示谢。 那少妇拉了马春花的手,两个女子到后厅去借房换衣。 三个武官互相一望,脸上现出特异神色,心中都在想像那少妇换衣之 时,定然美不可言。适才和徐铮斗口的那个武官最是大胆,低声道:“我 瞧瞧去。”另一个笑道:“老何,别胡闹。”那姓何的武官眨眨眼睛,站 起身来,跨出几步,一转念,从地下拾起腰刀,挂在身上。P5-9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