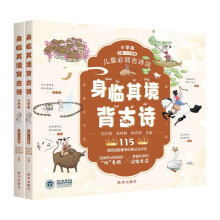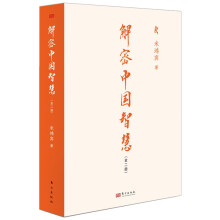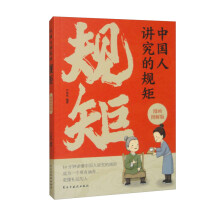《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
由上述可知,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将个人主义予以了最大限度的释放,而在它带来种种善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其自身难以消灭的恶疾。面对这些疾病,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文化界其实一直在试图予以解决。尼采的“超人”是想给失去了意义和荣耀的人重建新的意义和荣耀,但他仍旧是在个体上进行努力,这注定是要失败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意图还原人生活着的开放而真实的世界,但仍是从西方旧有的思路上去开拓,也始终无法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只有马克思主义注意到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再采取个体主义的自我观念,而必须将个体融入集体,才有可能使自我获得真实的意义。另外,现代的社群主义也重新发现了社群对自我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了美德对个人塑造的价值,从而促成了近几十年来社群主义和美德伦理学的兴起。
其实,在东方的中华文化中,有非常丰富的可以对治个人自我中心主义和原子化个人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中国,无论是儒家、道家、佛教,还是各种民间思想,普遍认为个体的存在是不能脱离社群和社会的,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自我观,从来就是人己相合的自我观念。构成这种自我观的主要内容有如下逻辑思路:第一,人和禽兽是不同的。传统中国对人的最重要的认识就是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珍贵就在于他和禽兽是不同的。禽兽有知觉、有认识,但是它们的感觉和认识只是最粗浅的同类认识,也就是说在它们那里只有同类和非同类两种感觉,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但是人类则不同,人类的认识能力更高、感受能力更强,人能为天地万物划分类型,所以有各种“名”的划分;人不仅会为同类而感动,也会为天地山川、草木瓦石感动。因着这两种能力,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各种群类的划分,从而可以构成一个由各种社群组成的社会;另一方面,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和谐互动,从而整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敌我的世界,而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可见,通过人禽之辨,中国古人确立了人的社会性是自我观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
第二,人和社群、社会的关系。如前所述,传统中国人认为,人因着理性认识能力可以将人群划分成不同的群类,从而可以构成各个不同的社群,小到家庭、家族,中到村落、社区,大到民族、国家、世界。同时,正因为人天然地具有这种能力,所以也意味着人不得不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社群之中,所以,人无法脱离社群而生活。而且中国人强调人的贯通一切的感受能力,所以无论是最亲密的家庭还是最疏远的世界,和自己都不是彼此隔离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种联系有亲疏之别,但即使是遥远的万物,也不是与自己不相干的。所以宋儒张载有“民胞物与”的说法,人的感受力,可以使人对他人、他物感同身受,所以一国之内的民众都是我的同胞,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显然,在传统中国人看来,人和社群乃至整个世界是关联在一起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并不独立于自己所在的从小到大的各类社群。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所在社群的完善和幸福恰恰是自身之完善和幸福的基础,两者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有了第三点,即中国传统中天人相参、人可以且应当参赞化育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有天、地、人三才之说,认为天、地、人各有其道,人在这个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人和天地一起使这个世界和谐、和睦而丰富多彩地运行。天道生生不息、流行不止,虽然一事一物有其荣枯,但是整个世界的生命洪流却是奔腾不止的;地道厚德载物、涵容一切,万事万物形形色色、各有所需,大地都无所差别地为他们提供滋养、润泽他们的生命;与天地相应,人道就是顺承自己的生命,担负起自己生存的意义,尽心尽力地在天地之间精彩而丰富地生活,从而使整个世界大生命圈更加和谐。也就是说,个体的独立生存,不仅是为了自身,还是和整个世界相协和的,所以个体自身的完善和社会、世界的完善应是和谐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