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阳光
我看中了国外的一幢房子,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巴玛苏罗。房子又高又大,四四方方,杏黄色的外墙,略有褪色的绿色百叶窗,古色古香的瓦质屋檐,二楼还有一个安装了铁栏杆的露台。我暗忖,过去的女眷说不定就坐在那里,轻摇着扇子,欣赏下面的风景。可如今楼下长满茂密的欧石南、枝蔓杂乱的野蔷薇和高至人膝的杂草。露台面朝东南,顺着眼前的深谷望去,远处是绵延至托斯卡纳的亚平宁山脉。每逢下雨或光线交替之时,房子的正面就会相应变成金黄色、黄褐色和暗红色;原来的红色墙壁渐渐模糊成玫瑰色,像一盒忘了收拾的颜料,在日光下慢慢融化。有几处石灰墙皮脱落了,露出粗糙的石头,墙壁原本的样子隐约可见。房子坐落在一处满是果树和橄榄树的山坡上,一条白色鹅卵石路蜿蜒而过。巴玛苏罗,是由巴玛(bramara,渴望)和苏罗(sole,太阳)两个词构成:渴望阳光。没错,这正是我的内心写照:渴望阳光。
家人一致反对我的购房计划。母亲觉得这想法荒唐之极,她故意将“荒唐”二字说得震天响。姐姐虽然很兴奋,却也忧心忡忡,好像我是个十八岁的少女,打算盗用家中的汽车,跟哪个水手私奔似的。我又何尝不是疑虑重重。尽管已经坐在意大利公证人办公室外的椅子上了。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我每一挪动身子,椅子上的马毛就会穿过白色薄棉裙,刺我一下。只有在紧张之极的等候中,人才会留心到这种细微的感觉。我瞟了一眼埃迪,想看看他在收据背面写些什么:帕尔玛千酪、意式香肠、咖啡、面包。这个人怎么敢在收据这样的重要物品上乱涂乱画?终于,一位女士打开办公室门,冲着我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通意大利语,语速堪比急流。
意大利的公证人和美国的公证人有着云泥之别。在意大利,公证人只是处理地产事务的法定代表人。我们委托的公证人曼图丝女士是西西里人,她个子不高,作风雷厉,鼻梁上架了一副厚厚的浅色眼镜,衬得绿色大眼跟风铃似的。她大声地念着冗长的法律条款,语速比我遇见的任伺人都要快。我一直认为意大利语是世界上最悦耳动听的语言,没想到从她口中说出来,如同岩石滚落陡坡。埃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我知道他是被这位女士的声音震呆了。房主卡特医生看到我们真的有意购买,似乎突然觉得自己的报价太低了。他肯定是这么认为的,而我们其实知道他出的价格高得离谱。事实上,我猜中了他的心思。那个西西里女公证人,一口气都没停,没有人能够打断她的话头,但是楼下小酒吧的老板吉塞普是个例外。他突然推开公证室暗色的门,举着托盘,满脸惊讶地望着里面面面相觑的美国客人。他给曼图丝女士端来上午的浓咖啡,她拿起咖啡,一饮而尽。房主想报两个价,合同上的价格低一些,而实际成交价要稍高。“理当如此,”他再三坚持道,“哪个人会这么傻,把真正的成交价公之于众。”他建议我们在公证处开一张支票,私底下则把款项分成十张面额较小的支票给他。
闻言,我们的中介马提尼先生耸了耸肩头。
我们雇来负责翻译的地产代理商,英国人伊恩,也耸了耸肩头。
最后,卡特医生只好无奈地说:“你们这些美国人,真是太死板了。好了,拜托你们别将支票日期写为同一天的,隔一星期一张,这样银行才不会察觉这笔大数目。”
难道他说的银行就是我去过的那一家?那个眼睛又黑又大的出纳,总是无精打采,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十五分钟才能处理完一宗业务。女公证人的话音停了,她理了理文件,塞进一个文件夹,起身送客。等钱和文件备妥之后,我们还得再度造访。
推开旅馆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意大利科尔托纳风格的古老屋顶一览无余,远处青黛色的基亚纳山谷迤逦。一阵狂野的热风吹过,使得正常人都不由得疯狂起来,而此时的我,正处于疯狂之中。我难以入睡。在美国也捣腾过几套房子,每次我都是把母亲的斯波德瓷器、一只小猫和部分盆栽往车上一扔,驱车五或五千英里,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掏出新钥匙打开新房门,便大功告成。当然,在你脑袋上方的屋顶就要更换的时候,难免心事重重,思前想后。毕竟,卖房子意味着必须丢弃一连串回忆,而买房子则是在选择未来的容身之所。没有一个住所是中立的,它势必对你产生影响。除此,还有那么多法律手续和种种突发事件等着应对。这一切都让身在旅馆的我,眼前一片黑暗,无所适从。
意大利一向是我心灵的指针。在我们租住托斯卡纳农舍的四个夏天里,买房的念头就在脑海中盘旋不去。初访意大利时,我、埃迪和另外两个朋友合租了一处农舍,自入住的第一晚起,我们就开始盘算四个人的积蓄凑在一起,能不能买下那幢站在阳台上望见的破败石砌农场。埃迪立刻迷上了意大利的乡村生活。他整天在附近的田里转悠,看邻居们干活。安托里斯人擅种烟草,这种植物虽然可恶却很漂亮。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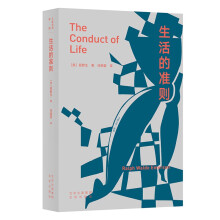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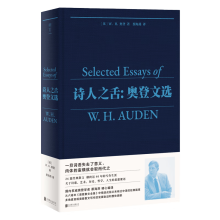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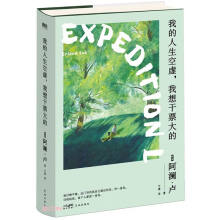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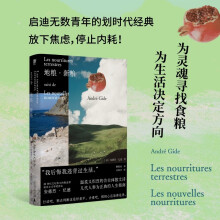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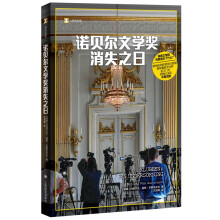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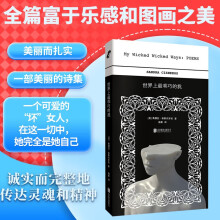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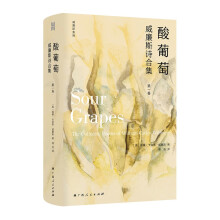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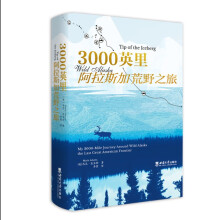
——《纽约时报》
★每一页都散发着阳光的温暖,它是为象征希望和重生的太阳献上的一份礼物。
——《泰晤士报》
★梅斯拥有无与伦比的表现力,几个世纪以后,巴玛苏罗的主人会在梅斯的餐桌上揭开陶罐的盖子,去想象、构思那遥不可及却又难以抹杀的历史片段。
——《洛杉矶时报》
★来自我们梦想中的意大利,依旧富有田园气息,依旧散发着不加雕琢的自然之美。
——《波士顿环球报》
★一首流动在空气中的诗篇。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