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色鹿·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阿玉》:
妈妈就掩嘴笑。妈妈的门牙微微前突,这使她笑起来老不自在。
冯叔叔和爸爸一块儿出远门的时候,天择和冯姨就成了家中的常客。
冯姨和妈妈着迷打毛线。毛衣打好了打毛裤,毛裤打好了打帽子。先给我们小孩打,打完了再打大人们的。空气中飘浮着红的绿的蓝的细绒毛,沾到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嘴唇上,吃和没吃过的糖块儿上。
冯姨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来问:“多少日子了?”
妈妈不看日历,她能一口报出爸爸他们走了多少天。
我和天择也关心这个问题,爸爸和冯叔叔回来会给我们带高级糖果,这是惯例。我们盼望他们回来也成了惯例。
有盼头的日子不仅是甜的,而且甜得五光十色。
那一年我们盼来的却只有爸爸,瘪瘪的大黑包网一样罩在他身上,他显得从未有过的消瘦和颀长。
“他呢?”冯姨手中的毛线活儿散了。黄色的毛线团骨碌碌从怀里滚到大腿跳下板凳蹦到地上。
天择拿它当足球,一脚踢到了后院空荡荡的麦场。
妈妈帮爸爸拿下包,爸爸顺势落到凳上,重得很。
“他呢?”妈妈的眉头蹙到一起。冯叔叔不回来是因为回不来了。
爸爸带着冯姨和天择出去了半个多月,回来天择就缩在墙角,成了另一个模样。
冯姨把乌黑的辫子剪了,短发束在一块白手绢里,刘海也掐到白发卡里。
冯姨不笑不说,目光直直的,稍稍转动就带出一串滚烫的泪蛋蛋,像疾风骤雨,挡都挡不住。
冯姨一哭,墙角的天择就挥动他的手臂,在眼睛上狠狠一刷,嘴巴一撇一撇的。
妈妈轮番抱他们。我干脆躲到麦垛深处,我怕我的眼泪跟着往下掉。
爸爸摔了香烟。他经常一根烟抽不到尾,就把天择拉到怀里,一遍遍抚摸他圆溜溜的光脑袋。
冯姨是冯叔叔从老远老远的地方,爬了好多山蹬过许多水带回来的。她几乎抢在天择之前成了孤儿。爸爸妈妈一合计,干脆把他们俩接过来住。
我不再吃天择的醋了,妈妈怎么亲他、爸爸怎么惯他我都不难过。我也不跟他分糖吃。我把糖果一股脑儿装到他口袋里。
渐渐地,天择的脸重又白胖起来,没事的时候,老拿妈妈和冯姨的毛线团当球踢,冯姨在旁边长长短短地叹息。
那天,爸爸从旅行包里掏出一只洁白的足球和一双白球鞋,天择兔子样欢腾。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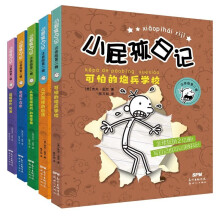




——文学理论家 刘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