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AA“特雷多美术馆玻璃展览馆”2006年
西泽当原广司先生在看森山邸与HouseA的时候,他提到就算将建筑朝向都市打开,也不认为建筑世界就可能不会损坏,由于我未曾有过这样的思考方式所以觉得非常新鲜,不过我今天却感受到了原先生针对森山邸所提出的看法。鬼石案虽然是开放的,然而非但建筑的丰富度完全没有被损害,感觉上还不如说变成了更深刻而丰富的存在才对。
长谷川产生了与“内外可以相互被看见”这个意义上的开放性层次完全不同的现象呢。我在这栋建筑物中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触媒性。走在外面的人们当然是如此,但风景本身得到了触发,而位于内部的我们的感觉也受到了触发。由于这个触发的方式只能够来自于个人的体验,因而是无法被记述的,但是我认为在这栋建筑物里的确有着那种在相互认识上源源不绝、不断更新的触媒性存在。
刚才,在健身房看到了使用着跑步机慢跑的欧巴桑。我总觉得因为一边看着玻璃对面的那些坟墓来慢跑,她们的人生观也会开始改变吧(笑)。感觉上这栋建筑物在无意识的层次上改变了周边的环境与居民。那和不断地进行再生的,“神道的时间概念”非常接近。我之所以会联想到神社建筑,是受到持续不断地产生的这种代谢性与触媒性所吸引的缘故。从这栋建筑身上感受到了与那相近的感觉。就算是从外面看不见的不透明的东西,妹岛先生不也是能够做出以触媒性作为机能的那种建筑吗。
金泽21世纪美术馆(2004年)由于具有文化的,或者说是推广启蒙教育的明确的空间计划,而且也比较容易加以响应进到那个场域的人们,然而在鬼石一案中,即便目的并不明确,但却改变了整个周围的状况。这栋建筑看起来之所以有那么一点激进(radical)就是这个缘故。我认为这或许就是如此震撼了西泽先生的理由之一吧。
西泽金泽21世纪美术馆这栋建筑物,的确可以看得见其响应空间计划(program)的形式所制造出来的轨迹。相较之下,鬼石案当中则没有这个部分。看起来并不是从program所创造出来的结果。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上它仍是栋在根本上与program或人们的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
长谷川我认为将建筑朝着都市加以开放的时候,所必要的并不只是对于周遭的宽容,还在于企图将周围加以改变的意志。因为我是如此强烈地propose(提案)了,所以希望你也能够参与。我认为让空间能够具备宽容以及某种强制性的力量在里头的这件事,就是一种新的program。
我从时尚设计师川久保玲身上也感受到了与上述相近的特质。有着通过作品来改变周围的意愿存在。不过就川久保小姐的状况来说,由于表达这个讯息的媒介是衣服,因此可以马上被反映出来,而鬼石案则比较属于那种随着时间的经过而渗透的东西。
不过就算如此,在妹岛与SANAA的作品里的建筑体验,每个都很不一样呢。
西泽这个鬼石案,和洛桑案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妹岛是的。在鬼石案当中,借由曲线使得内部与外部在平面上接近与远离的现象得以发生;而托雷多美术馆的玻璃展览馆(2006年),则做到了远方场所与邻近场所相互重叠与消失的那种外部与内部的关系性。在NewMuseum(2007年),则是试图在断面的方向上来思考上述的关系性。至于洛桑的RolexLearningCenter一案,我则认为是把在各个平面与断面的各种零星的尝试做出了整体性的整顿。因为在地板出现了曲面的缘故,所以我认为这样的现象也会在立体的向度上产生。
长谷川洛桑一案是借由如同在丘陵般的场所中上上下下的这个动作,想象着对面的风景可以看得到或看不到的这种体验的实现。此外,有着各种大小的中庭呢。从窗户往外看,便可以看得到在中庭里闲聊的人们的身影。
妹岛是啊。在中庭有Café,而在它的对面又可以看到别的室内景象。
长谷川外面的景观是怎么样地被感受的呢?
妹岛从建筑物的入口进去的那个瞬间,迎面而来可以看见的是远处的山脉与湖泊,然而随着地板的起伏也会突然变成远景。就算是在高处,然而因着屋顶的下垂而看不见外面、或是相反地在比较低的地方也会因为屋顶的上升而得以感受到位于外部的气息。
长谷川那是将墙壁加以曲线化以及将地板与天花加以曲线化的意思。在那儿所发生的体验似乎很可能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呢。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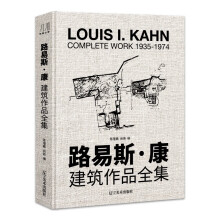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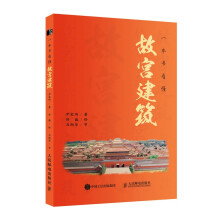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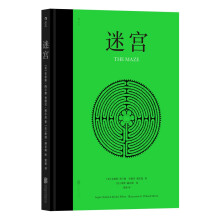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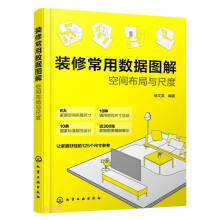
——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
西泽立卫致力于创造“在尺度和规模上都超越建筑物本身的景观式建筑”和“体现时空关系的建筑”…… 上述两项特质使得西泽的建筑总是能够不断营造出新鲜的空间体验。
——网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