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虚构到现实
民族主义要在一个社会中发育成长,这个社会,至少是其具有最敏锐的洞察力的成员的心中,必须已经形成了它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最起码是一个民族的雏形的形象,借助于某些凝聚一个民族的普遍的要素——语言、种族起源、共同的历史(现实的或想象的)——那些受到较好教育、具有更多社会和历史关怀的人士必须对这些观念和情感做出相当明确的阐释,而这些观念和情感,在普通民众的意识中还是朦胧模糊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以赛亚?伯林
一、权力结构:精英和民众
……
在民族主义思想家那里,民族主义就被表述为一套理性化的观念,具有系统的历史论据、政治与文化理由、甚至哲学依据,但有时他们的理论的基石多半是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假设,只不过经过了理论性的整理和修饰。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就是如此。民族意识是由知识分子和学者宣扬起来的,并在有教养的城市市民阶层中逐渐普及开来,其核心是一种虚构的共同出身、共同的历史结构以及具有同一语法结构的书面语言等。有了这种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就成为一种可能。
精英的处境和心理状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精英阶层受到伤害,无论是利益上或是心理上,以民族主义方式的反弹就会有巨大的杀伤力,他们以一种激情创造民族主义的话语,不管是不是弥天大谎,但他一定要表现出他确信自己正在献身于一个伟大的“民族”,因而毫不动摇地确信,他自己是为民族的前途和利益奋斗的。当然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精神挫伤感也不完全是一种幻想,他们确实深切感受到外来文化和势力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冲击,他们最敏锐地看到了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宗教之间的不相协调之处,他们不断地甚至完全被排除在实际权力之外。于是,他们中最有天分、最具独立精神的人士就用越来越强烈的叛逆思想和行为,对他们的世界所遭受的破坏作出回应。
伯林是这样谈到德国民族主义者的:
他们把受到伤害的文化自豪感与某种哲学—历史观结合起来,用以疗治民族所受的创伤,并创造了某种内在的抵抗对象。最早是一小批有教养、心怀不满的仇法主义者,然后,在法国军队带来的灾难和拿破仑的一体化政策的冲击下,少数的不满演变为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这是民族主义激情的第一次高潮,这里面有狂热的学生沙文主义,焚烧书籍,秘密审判叛国者,完全失控,兴奋过度,甚至厌恶歌德、黑格尔等冷静的思想家。后来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多多少少受到德国人的豪言壮语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跟德国人基本类似,因而也导致了类似的精神郁闷,当然最后也就采取了同样危险的治疗手段。德国之后是意大利、波兰、俄国,然后是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和爱尔兰人。
民族主义运动所开发的社会资源,以及以主权为象征的民族国家利益,并不是由普通国民所代表的,这些资源和利益也并不是均等地分配于每个人身上的。民族主义所带来垄断权力、利益分配,更有利于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各阶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兴奋点有着强弱不同的分布。知识分子和精英推动民族主义潮流,创造构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操纵民族主义政治,毫无疑问,他们也从中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那么,从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分配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也可以看作是维持既得利益或开发新的社会资源的功利主义策略。任何政治家无一例外都会如此宣称,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的一切决定和行动都是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这样的表示是民族主义政治的内在要求,因此他也就有了号召群众的合法性。工商界可以用民族主义抵制进口,推销其商品。学术界可以提倡文化传统占有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任何现实的政治都必须在民族及国家的范畴内操作,而任何民族主义都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民族”作为臆想的共同体,其起源不涉及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但也恰恰是这个原因,“民族”这一概念极大地模糊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更模糊了权力操作的利益关系。
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人民应该具有共同的文化并服从该文化的精英的统治,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包含着把民族与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者视为一体来加以维护的功利因素。以民族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都是以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来谋求政治权力的。从历史上看,还没有一种民族主义运动不最终指向政治权力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是一个统一国家内的议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权力。达尔就认为领袖们弘扬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因就是使他们的领导拥有合法性。
民族主义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历史生存基础,他们可以拥有不同的、针锋相对的政治观点、世界观、社会改革方案,但在民族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给追求权力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政客提供了一个政治操作的舞台。如何操作,则取决于他们的道德水准、价值取向、世界的视野和知识结构。由于社会、政治、文化危机等原因,自卑、焦虑、失落、排外、无所适从、对专制秩序的认同等等心态就可能会主导精英和知识分子,从而导致整体精神大逃亡和道德底线的崩溃,他们所创造的意识形态往往狂妄自大。虽然可以很天真地说,诉诸诚实而正直的良知,意识形态才会博大宽广。但从价值和道德来要求民族主义精英是一件再危险不过的事了,因为精英们最关心的是政治权力和话语霸权,而价值、道德和原则立场常常是可以改变的。奥威尔描述了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形形色色表现和精神特征,各种不同的,甚至表面看来截然对立的思想潮流中的共通之处:
他们面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原则和立场是不同的,只要一涉及到民族主义忠诚,他对现实的理解、他的文化品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道德感,就完全扭曲了。例如,在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等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可以转换的,这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倾向。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中间的民族主义比普通人更明显。
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是没有信用和忠诚可言的。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是精英自己创造的神话,亦即自我表达方式。奥威尔认为,“民族主义者并不必然意味着效忠于某个政府或国家,也未必效忠于自己的国家,甚至他所为之奋斗的对象都未必在现实中存在。举几个明显的例子,某些宗教、无产阶级、白种人等等,都是某些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所钟情的对象,但这些对象的存在却大成问题,而关于这些对象的定义,恐怕还没有获得公认的。”他特别指出这样一种现象,不少民族领袖或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其实并不属于他们为之奋斗的国家。有时,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更多的时候,他们来自其民族性大成疑问的偏远地区。比如斯大林、希特勒、拿破仑,泛日耳曼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英国人张伯伦的创造。这也许多少能够解释,对于精英来说,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获取权力和名声要比价值、立场和原则重要得多。
需要注意,奥威尔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固然揭示了精英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但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发源,也与民族主义有着非常内在的联系。而奥威尔把历史上产生的自由主义高度道德化普适化,以此谴责精英知识分子,这种努力也许存在着内在的悖论。
政治权力的斗争,无论发生在议会或者政党内部,常常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当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或者受到了来自经济或社会方面强大的压力,就非常倾向于向民族主义要资源。此时国际争端会成为权力斗争的有力杠杆。强硬派(往往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话语资源上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他们利用“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类的口号赢得广泛的支持,通过宣扬爱国主义增加对权力的控制或提高在权力斗争的优势。即使没有外敌入侵的事实,权力斗争的需要也可以非常方便地制造出“侵略”和“压迫”的宣传。只要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这一类威胁统治阶层的因素存在,民族主义就永远会被利用来化解统治危机的手段。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常常用“国家”、“民族”的名义来掩盖专制、腐败,拒绝实行政治改革,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
“权力斗争总要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现象是普遍的:在政治权力需要得到国际支持的时候,任何条约都可以签订;当国际问题涉及到权力统治的时候,国际争端就变成了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问题;当权力斗争需要诉诸民间支持的时候,政策的分歧就会以“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话语表现出来;当权力斗争还处在潜伏的状态,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而会受到压制。权力斗争就是权力斗争,这在任何性质的国家政治中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但是,“政治权力斗争是民族主义的全部秘密”的说法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精英和民众互动的关系。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广泛的文化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说到底是民族大众性质的。对于民族大众,民族主义是一种激情支配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激发大众爱憎、造就大众理想的信念,是以实际和想象中的民族区分为界的认同感以及排他意识,其最终的终目的是要民族大众做出尽可能大的物质、精神以至生命的奉献。民众不需要系统精细的理论思想,最能激励和动员他们的是感情和口号。只要民族主义思想一经转移到大众,便大致变成了简单化的信条形态,原来一盘散沙的民众就形成乌合之众;一旦民族主义思想转变为组织,乌合之众就会变成冲锋陷阵的洪水猛兽。尽管他们对文化和历史知之甚少,但民族主义运用宗教、文化、传统、历史和语言来操纵神话、象征和情感,构成了简单易懂的“民族”知识,从而极大地操纵民众情绪。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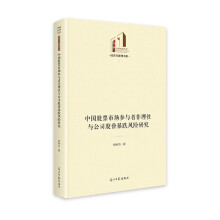

——《人民论坛》
★在民族国家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民族主义也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美德。但同时,民族主义也不时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