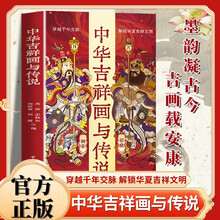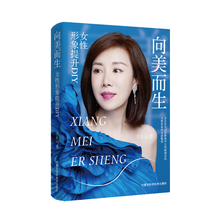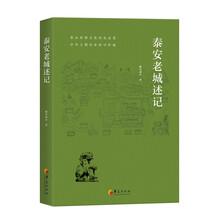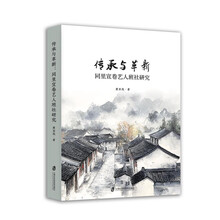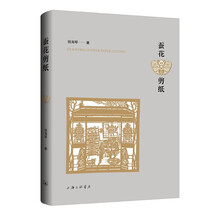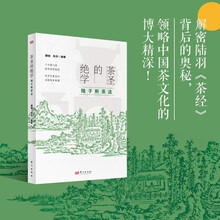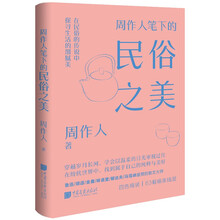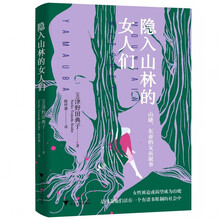《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系列:中国古代战争》:
可见,在两军对阵中,战将和士卒要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仅要戴盔披甲,而且要有高超的武艺。据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的武艺一向分十八种,而十八般武艺要想件件皆通,在搏斗中武艺高强,这确实是桩不容易的事。
《武经总要》记载,公元1000年,宋神骑副兵使焦僵献使用的铁槊,重15斤,在马上挥舞如飞。还有相国寺和尚法山,还俗从军,用的铁轮拔,浑头33斤,头尾有刃,是一种马上格斗的有利武器。《五杂俎》上说:“人有千斤之力,始能于马上运三十斤之器……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举动而已”。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对部将的武艺训练,要求极其严格。《金陀粹编·遗事》记载,有一次岳飞的长子岳云,练习飞马冲下陡坡,不慎马翻人仰,岳飞大怒说,前方大敌,亦如此耶?将岳云责打100军棍。在岳飞的督促下,岳云很快地成长为一员所向无敌的勇将,臂力大得惊人,能把两杆好几十斤的铁锥抡动如飞。1134年,16岁的岳云勇冠三军,攻随州,手持双锥,首先登城。
邓州战役中,岳云又捷足先登。1140年,岳家军的最后一次北伐,克蔡州,据颍昌,复淮宁,得郑州,占洛阳,战绩辉煌。岳云都是骁勇善战,屡建殊勋。在激烈的颍昌之战中,岳云先后10次杀人敌阵,身受100多处枪伤,和将士们都“人为血人,马为血马”,终于赢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抗倭名将戚继光,也非常重视部队的训练,《纪效新书》中对这方面有详细的叙述,主张“平时所使用的器械……当重于交锋时所用之器”。
这样,“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械所欺矣”。此外,戚继光在练武时,采取“足囊以砂,渐渐加之”,战时将砂囊去掉,行走时自然轻便自如。平时习战,人必重甲,战时换上轻装,行动起来就迅速。他把这些做法叫做“练手力”、“练足力”和“练身力”。古人练武,不仅讲求实效,采用从难从严的训练方法,而且非常重视实践。在《练兵实纪·储练通论》中,有一段论述叫做“练真将”。练将,就是训练军队的干部。练真将,就是强调指挥员要有真实本领,经得起实战考验。戚继光认为,一个指挥员,固然要精通“韬略”之类的兵法,反对不学无术,但是这还不够,还要把他们放到“伍问”去锻炼,出战时放到战阵中去考验。只有经得起锻炼和考验的人,才能正式任用,这样才能练出“真将”来。对于士卒的训练,也是本着讲实效、重实际。在练武时,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着手。因此,古代许多有名的将领都是鸡鸣即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持之以恒,从不间断。
这样,临战时才见敌不畏,骁勇异常。
在古代的战争中,不仅要求人们有熟练的武艺,而且要求军队有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孙子说,军队的行动“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行如雷霆”。又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公元874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风驰电掣,出无定,克洛阳,破潼关,下长安,近10年的时间,这支起义部队转战中原,南征北战,打了许多出色的仗,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行动迅速,猛打猛冲,采取先发制人,给统治者措手不及,取得了辉煌胜利。成吉思汗用兵的神速是驰名中外的,蒙古兵在进攻之前,先派“游骑”深入对方境内一、二百里,以侦察虚实。
因蒙古军行踪“飘忽”,常使对方疲于防御。在交战过程中,成吉思汗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旦探得对方空隙后,就大军长驱直人,势如破竹。如遇对方城防坚固,兵精粮足,在短时间内不能攻打奏效时,就采取神速绕越而过,或者留少许兵以牵制,从不恋战,待攻占了周围城寨后,再驱使俘虏充当前锋,回师总攻,一举而破之。
在短兵相接中,有了熟练的武艺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可以说具备了赢得胜利的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首要的是人心向背,看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个道理。此外,还需要搏斗中具有机智和勇敢。就是说,不是死拼、硬打,而要打得巧妙。会用正兵,也会用奇兵。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之。”公元115年,羌人侵犯武都,安帝派虞诩为武都太守,出兵抵抗,到了陈仓(今陕西宝鸡)被羌人所阻。虞诩暗自打量:敌众我寡,不宜硬拼。便想出一计,命令士兵暂不前进,扬言要向朝廷请拨援兵,待大军到后再出发。
过了几天,令士卒将原来一个灶煮的饭,改为两个灶煮。次日,又改为四个灶煮。一羌人远望烟火逐日增加,便相互传开,议论纷纷,汉兵大军已到,若不早退,将被围歼。因此,便不战而退。虞诩乘羌人撤退的时候,率3000轻骑追赶。当与羌人交战时,先令士卒以小弩发箭,故意表示装备很差,诱羌人来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