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纳兰容若,仿佛是一个注定为孤独而生的词人。而他,一生都在诠释着这种孤独,如若诠释他的追求“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这首写雪的词,宛如他终生的写照,关山万里,雪凝结天与地,然而雪花轻浮飘荡、居无定所的模样,仿佛不该是君子所喜爱的。但他却独爱雪在孤绝寒冷至极时绽放的样子,它无根无芽,却跳出尘世之外,不同于人世间那些娇弱秀美的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纳兰容若 《采桑子》
落笔成诗时,容若随同康熙帝巡视边疆。塞外风景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点点滴滴,都同他所熟悉的京城或江南大相径庭,词人的眼界与心胸,因此而大大开阔。然而,纵使是此时,他也不曾忘记萦绕在心怀的那个身影——谢娘,古人用来通称自己所爱慕女子的称呼。在雪中漂泊的旅途里,回忆渐次涌上心头,他想起她的温柔,从别后,忆相逢,已是千里之外。寒如泣血的月,随着沙风呼啸凄厉的胡笳声,大漠流沙,风雪走石,孤独的身影犹自徘徊,仿佛早已和周遭的悲凉融为一体。
而他终究会走向何方?是终点,抑或是起点?就让我们静静跟随,一探前尘,追寻遥远时光间,宛如传奇的那一刻。
顺治十一年,腊月十二,京城一个寒霜清澈的日子。凛冽的北风,并未摧残去帝都的繁华,天子脚下,依旧一片喧嚣。烟火人家,岁月飘零。年轻的公子走进京城里香火最为鼎盛的广源寺,眉目淡然,步履清逸,一抹骄傲萦绕发梢,就像是与生俱来的玉饰,令他从此与众不同。
香火迷烟染上眉眼,虔诚祈祷的香客如流水在身侧静静流淌,他依稀淡淡注视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谁,一个对于此时此刻的他来说无比重要的人。终于,那个人出现了,佛衣、白眉、如一尊被遗落在凡尘的佛。年轻公子终于露出一缕笑意,走上前去,合手行礼:“法璍大师。”
这是一位行事怪癖蹊跷的僧人。当然,也是一位佛法高深的大师。这使得他一开始成为广源寺主持时就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他们如追逐星月一样,涌入广源寺,请求他前去做法事,甚至只是为一个小物件开光做法,为此他们开出了极高的价码。面对这一切,法璍大师岿然不动,他不动声色地拒绝了一切请求,甚至告诉他们——佛祖早已死去,流转在人世间生生不息的不是佛祖万能的庇佑,只是一颗名曰佛法的种子,追寻佛法,倚仗他人的力量将会一无所获,唯有自己锲而不舍地寻找、努力、采撷,尘世的罪孽方会消除,苦海的无边方会浮现一叶舟楫。
这样的言论,并不能阻止凡夫俗子们对既有方式的惯用——天底下何止一个得道高僧。既然法璍大师不愿“帮助”他们,自然会有其他相对循规蹈矩的大师愿意伸出援手。他们很快抛弃了曾经执迷的大师,转而奔向另一场自以为的“救赎”,他们只需要一个轻而易举得只要付出一些金钱就可以抵达的场合,聆听、佩戴、虔诚或自以为虔诚地侍奉佛祖,大约这样,就能消弭所有原罪,获得永生幸福。
法璍大师的门,长久地对这些愚昧的人们合上了,时光洗去了对他犹豫怀疑的信徒,却留下了持久和意趣相投的朋友。这其中,便有一位纳兰氏的公子,彼时,他只是一位大内侍卫,大师却在这张年轻而文秀的脸上,看出了常人罕见的坚毅与沉静,他的人生,绝不会局限于一个小小的侍卫。大师如是想着,对这位公子,敞开了一扇偏僻的门。
今天,公子并不是来讨论佛法,也不是来同大师品茶论道的,他脸上淡淡的喜色出卖了他,他迫不及待地开口更是令大师会心一笑,几乎是急切地,他请求大师为家中即将诞生的孩子取一个名字。虽然他知道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符号,可他坚信名字也在冥冥之中,预示着一个人的一生。
面对初为人父的年轻人,大师的一言一句都深刻如佛偈:“明珠,你若是相信,那么一切便会是真实的,你须相信,终有一日你终究会成为一颗耀眼明珠,无人可直视你的光彩,你的夺目,将永远地镌刻在这个朝代的历史上。”
“而你的孩子,也将会用一生,来完成名字赋予他的使命。”
明珠若有所悟,他知道,他此行的请求大师已有答案。果然,法璍大师笑道:“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这句话自《易经》而出,你可知道它的意思?”
年轻人颔首,道:“虽然我不过是一介舞刀弄枪的侍卫,却也稍通文墨。这句话是乾卦里的内容,说的是君子之行。君子的一言一行,都是在成就自己的德行。而这些东西是外显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听到的。”
听完年轻人的解释,法璍大师满意而赞许地说道:“好!极好!我想你的第一个孩子将会是一个男孩,他的名字,便叫作成德。”
“成德……纳兰成德……”明珠低声默念着这个名字,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这个孩子,将用他的一生去完成君子之定义。这个名字,他很喜欢。
不日,妻子临盆。诞下的果然是一个健康的男婴。他被取名为纳兰成德,小名冬郎。后来因太子出世,乳名保成而改作性德,未久,太子取名胤礽,性德依旧改回成德,然而一年的时光,已经让人们叫熟了性德,便也随之而去了。家中的大人们,却不常唤大名,总是叫他冬郎,冬郎。
冬郎生得十分可爱,不出月,就能睁开眼睛,溜圆乌黑地注视着人们,极可人疼。初为人父的明珠经历了迷蒙和喜悦之后,早已在心中默默做好了对孩子未来人生的规划,雏凤清于老凤声,他希望日后这孩子,能够超越自己,成为家族更有力的支柱。
这句诗,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给外甥韩偓的,韩偓是当时名声在外的神童,一日,在李商隐的送别宴上,十岁的孩童登高作赋,为李商隐送行,四座皆为之震惊,李商隐亦是为韩偓少年早成的才华动容不已,他亦写诗与韩偓作答,其中便有一句: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而韩偓的小名,便叫冬郎。
明珠希望长子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孩子,诚然完成了这个愿望,然而,他所完成的,却并非是明珠所寄托的。他更像是沿着唐代神童韩偓的方向,走向了一条这个家族所陌生和不解的道路。多年后,当他的朋友戏称明珠的犀利眼力来称赞他的诗词时,他不以为然地笑道,大约家父当时不曾想过那么多,叫作冬郎,无非是因为出生在冬天罢了。
此冬郎,同唐朝的冬郎却不无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年少显才名,恰好都在十岁的年纪,韩偓十岁一诗惊四座,流花飞柳于庭前,纳兰亦是在十岁时,写下一首月食诗,以此显露出他令人惊诧的才华。
康熙三年,正月十五。正是元宵,本来应是月上黄昏灯花流影的时节,却发生了月食。纳兰有感而作,写下了一首《上元月蚀》:
夹道香尘拥狭斜,金波无影暗千家。
姮娥应是羞分镜,故倩轻云掩素华。
满城喧嚣,灯影簇簇,道路两旁都是密密的人影,染出一道狭长香径,千万家都在翘首以待,等着月色光华耀眼人间的那一刻,然而久久的等待后,等来的却是月光黯然,天地失色。大概是月宫中的嫦娥仙子看到人间如此热闹繁华,一时害羞,不愿打开明月之镜,所以用轻纱薄云,掩去一袭素衣芳华。
谁曾想到,这竟是一个十岁孩童写出来的诗。平仄,格律,均无出错。实际上,清朝时的字词发音同唐朝已有很大变化,想要写出一首严格的近体诗,必须熟记平仄音,甚至要通解唐代发音,在严密的格律规则中,作出这样一首精彩的诗,也难怪他年少便有才名流传于偌大京城。
多年后的元宵,京城再度发生月食,时年二十八岁的纳兰容若又写了一首词:《梅梢雪•元夜月蚀》:
星球映彻,一夜微退梅梢雪。紫姑待话经年别。窃药心灰,慵把菱花揭。
踏歌才起清钲歇。扇纨仍似秋期洁。天公毕竟风流绝。教看蛾眉,特放些时缺。
京城里彻夜灯火通明,温热得梅梢的积雪都微微消融。仙女紫姑正在同经久未见的友人把酒言欢,月宫里的嫦娥却回忆起了当初窃药长生一事,羞惭得不愿露出真容。月色被一层薄纱笼罩,元宵岂能无月,地上的人们踏歌击鼓而来,想要将吞噬月光的天狗驱逐,终于使得明月柔满,一袭清辉照耀大地。向来是天公心性风流,想要瞧一瞧那一弯如眉的月,因而特意令月食蒙住了月亮。
这首词作同十岁时写下的《上元月蚀》自然不能相提并论,此时的遣词和意境,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然而,当年《上元月蚀》的惊艳,依旧令那十岁孩童在生命开始的最初,便流光溢彩。
年幼的雏凤,已展露出惊人的光彩。仿佛早已命中注定了明珠当初那句话:他相信,名字亦是人生的一种预示。在他的长子身上,这句话宛如箴言。名字的纠缠,跟随了那个孩子一生一世。不论是成德,抑或是冬郎,都一如预言,在人生的每一寸光影里,悄然流动,宛然成形。而那两个名字,都不是他的朋友们,和后世的我们最为熟悉的名字。
朋友们都不时常叫他纳兰成德,也不像家人一样随意地唤他冬郎,往来信中款款展开,约莫都是一声:“容若。”
容若,他的字,亦是他的诗。纳兰容若,连在一处,便是一阕永驻秀词。山水清绝,风月萦怀,这四个字的名字,叫多少人念了一生,痛了一生,伤心了一生。看尽过客千帆,走遍漠北江南,依旧解不开心中一斛清愁。
或许当真是上苍预知在前,这四个字,分明都是再简单纯净不过的,合在一处,却洇开轻雾般的悲凉,轻淡的,柔婉的,苍白而诗意的,便如同,他的一生。
他是一方墨砚,在千万尺下深蕴的泥土里埋藏了多年,被采石人无意发现,挖掘,由雕刻师精心镌刻,置于宝匣,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柔润的光华,占据了每个人的心头。
身处繁华深处,一切都是最好的,衣是绫罗锦绣,食是珍馐佳肴,住是楼阁广厦,出门是千里良驹,这里的富贵不是烟云,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可以感知和触摸,也可以给人带来暂时的快活。短暂的快乐过去之后,便是难以挣扎的虚无和寂寞。在这里,清风不能愉悦地滑过心头,岁月不能圆润地流过紫竹林,突兀的气泡如流沙,总是抚不平、挥不散。锦绣罗帐中的贵公子,没有一日不感到惆怅和凄凉,唯一给予他慰藉的,是青玉案间一寸墨色和一叠宣纸。
唯有它们,才是这丹朱人生的真实依托。他叹了口气。他知道,当他如是思考时,命运之于他,便永是不得圆满的悲凉。
第三节
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
古人说伤春悲秋,自古以来,伤春的诗词数不胜数,杜牧写过“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东坡笔下有“花褪残红青杏小”,他们笔下的春意,孤凉,飘摇,如雁过江心,徒留一片涟漪的寂寞。而到了纳兰笔下,一切又有了新的味道。
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窗间伴懊侬。
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
——纳兰容若 《采桑子》
纳兰的伤春,是冷清的,幽寂的,好比寡欢了一夜的梨花,蘸着春露的寒,委顿哀婉,一轩红影摇曳,剪碎了遍地欢情。
春日的清浅时光,他推开微湿的窗棂,清风迎面,吹来一袖的红粉香浓,其实再浓的春风也是慵懒的,用一个时节褪去凛冽,终究换来四个月的清婉娇柔。这样的春光,他似乎没有什么理由用来伤怀,就像生于锦绣家族的他,在世人眼中,完美到极致,便不应有任何负面情绪。
寻常的人们,又怎么会明白高处不胜寒的孤绝?又怎么能看到他心中的风景,也因心绪的起伏,随之愁肠百结。
容若记得,幼年时,自己也是有过一段极好极好的春光的。他的奶娘姓吴,大人们都叫她吴妈。吴妈读过一点书,四书五经也看过一些,这在下人里十分难得。更难得的是她有一肚子的好故事,古来今往的故事、神话、寓言,她没有不精通的。年幼的纳兰便时常缠着吴妈,要她给讲故事。
最初的启蒙,通往文学殿堂的那扇门,是奶娘为他开启的。在她怀里,小小的孩童听完了大禹治水,听完了嫦娥奔月,也听完了桃园三结义,还背完了人生中第一首古诗,是李绅的《悯农》。他的童年,仿佛跟寻常孩子的一样,并没什么出入,一样酷爱传说中的开天辟地,一样纠结故事里的生死哀乐。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故事和传说,并未随着时光的老去而凋零,它们的芬芳,在漫长的光阴里升腾,落地,发芽,结果,终于酝酿成纳兰灵魂中最重要的一魄。
对文学的敏锐,使得纳兰容若养成了自小细腻的性子。五岁的时候,家里来了许多同龄的朋友,一群孩子聚在一起,踢毽子捉蛐蛐,肆意玩乐。路旁长了一株李子树,结满了果子,其他孩子们看见了,纷纷跑过去摘果子,唯有纳兰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一动不动。路过的亲戚看到了,不由好奇。五岁的孩童奶声奶气却不失逻辑地回答,如果那个果子又大又甜,早有路人去将其摘取,哪里能够留给一群孩子呢,那果子一定不好吃。
亲戚半信半疑,亲自摘取一个试吃,果然又酸又涩。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有这样敏锐的洞悉力,真是个无比聪明的孩子。
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纵使是在寻常人家,为人父母的也愿意千方百计送入学堂,或许日后一鸣惊人,从此青云直上。更何况纳兰生在王爵清贵之家。这种屹立在朝堂之上多年岿然如磐石的家庭,自然深知教养子弟的重要性。明珠,也不例外。
顺治十七年,纳兰容若六岁。明珠为长子请来了一位先生。先生来自遍地文人满城书墨的海宁,学从黄宗羲,诗从钱澄之,在江南一带素有“才子”之名。后来,因为屡试不第,遂绝了仕途之意,更将名字改作査慎行,意在谨言慎行。对仕途心灰意冷后,查先生便很少留在家乡,反而天南海北到处游历。
幸而査家是海宁名门,家境殷实。在明珠府做先生,实在是被明珠的一腔父爱打动——明珠为表诚意,先后亲自给査慎行写了三封信,恳求他来府中为犬子西席。到底盛情难却,未久,査慎行赴京,成为纳兰人生中第一位正式的师傅。
在先生的教导之下,纳兰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很快,他就能够倒背如流。学生聪颖,做师傅的自然也自豪。明珠事务繁忙,很少来查看长子的学业,然而少有的几次考校学问,却比先生更严格。纳兰容若每一次,都回答得毫无纰漏,几乎完美。先生倒是慈师,时常向明珠夸赞。只有这时候,严父眼中才会流露出些许笑意,对年幼的纳兰容若来说,那就是最好的嘉奖。
其实他自幼便很仰慕父亲。或许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曾有过一段将父亲当成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的时候,时间或长或短,总觉得天地之大,父亲是无所不能所向披靡的,世界上大约没有什么能难倒他。纳兰容若幼时,也曾满怀景仰,想要像父亲一样建功立业,备受器重,是门庭之光,也是国之栋梁。不,实际上,他想要的比父亲还要多,他不愿徒手安逸于富贵,也不愿单纯地以祖辈的余荫,走上一条被彻底安排好的路。
真正的成功,不该是如此。它从来都需要十年寒窗的头悬梁锥刺股,需要无数血汗堆砌,不论寒暑春秋,自己的双手,才是叩开成功之门的真正秘籍。纳兰容若深知这个道理,他未曾沉溺于锦绣飞灰,未曾流连于富贵烟华,如果可以选择,他愿意做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可以吟诵《古朗月行》,也敢挑起一肩泰山。幸好,他是可以选择的。
当他明白这一点,并打算将此践行时,他愉快无忧的童年,便在那一刻,彻底结束了。
在习文的同时,他学着蹲马步、倒立、舞刀弄枪。祖辈们是在战马上挣下的这份家业,身为子弟的后人们也不敢忘却这一点。习武比不上习文环境优渥,纳兰容若却都一丝不苟地去完成每一个动作。三伏天,他在阳光下挥洒着汗水;三九天,寒冷的北风记录着他的坚持。有欲望,便必须付出代价。他虽然还年幼,却比谁都懂得这个道理。
这些事情,他都做得很好,并不曾辜负过谁的希望。然而,做得好,却并不代表真心欢喜。纳兰容若,注定是一个文人,一个以笔惊艳了世间,温柔了岁月的文人。关山戎马,踏破贺兰山阙,这些激荡在胸臆间的情怀,他渴望,却不深爱。他的家族,教会他用生命去渴盼建功立业,而他的灵魂,却教会他用骨骼去热爱经卷墨色。
启蒙读物,他很快读完;他开始翻阅父亲书房里的藏书。《诗经》《楚辞》《春秋》……童年里的岁月,之于他,是一行行水墨的颜色,是一节节娟秀或隽永的篇章,是一卷卷漫长而恢宏的过往。躲藏在书房里的纳兰容若,时常会忘记时间,仿佛他正行走在一个浩瀚无边的时空,世界翻手覆手随意浮沉,日月星辰都只属于他一人的灿烂。在这里,他忘记了进食、休息,甚至忘记了光阴的流动。碧色狭窗里,潇潇细雨间,他渐渐长成了翩然如玉的少年。
时光悄然轻逝,如天地雪夜里无声流逝的河流,恍惚里完成了生命的轮回——有人出生,有人成长,有人死去,在同一个瞬间。当那个关于死亡的消息传入明珠府时,少年容若一时间陷入了苦苦的疑惑和追寻里。这场死亡的主角并不是他的亲朋好友,然则那个人却同他的生命有着息息相关千丝万缕的干系,伴随了他一生的名字,源于那个人之口,而他人生的星轨,仿佛也因此画就。
死去的那个人,是广源寺的法璍大师。
大师素来是一个我行我素之人,他不在乎人世的言论,毕生都在追求一个“真”字,真心,真情,真我。情深不寿,刚极易折,这样的人到底不容易行走于世,哪怕他已遁入空门,了却青丝凡尘。对思想舆论控制极严厉的清政府以“妖言惑众”的罪名,闯入清净佛门,面对如豺狼虎豹的官兵,大师如有预料,只是淡淡反问:有何证据。便合掌安然走进室内,不再理会世外所有喧嚣。
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出来。
官兵们碍于大师清名,一时也不敢贸然闯入。等到几日后破门而入,却发现法璍大师早已在房中自缢身亡。当时的情景,几乎吓傻了一群人。大师自缢于横梁,脚下却没有任何垫脚之物,地上唯有几支烛台,围成一个圆,烛火早已熄灭,冷冷的红蜡流淌了一地,像泣血的泪。
一时间,这桩自缢案成了京城的无头公案。任是衙门里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法璍大师究竟是如何自缢的。当时官兵将广源寺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大师房间,他断不会死于他杀,那么横梁那么高,他究竟是怎么上去的?
少年容若亦是不解。想了很久之后,他从父亲处得知,从容奔赴死亡的法璍大师,是借助了冰。是的,京城里的人向来都有在地窖里储存冰的习惯,大师以冰为垫脚石,自绝而亡。在他死后,燃烧的烛火,融化了冰,熏干了水渍——一切,仿若一场空寂,来和去都是了无痕迹。
大师用他的死,精心布了一个局,愚弄了无知可笑的政府。他以死亡,向黑白浑浊的世间,最后一次发出了有力的嘲笑。或许大师也知道,有人会为自己的死亡发出阴冷的笑意,也有人会因此觉得内疚追悔,甚至悲伤沉痛。但世间喜笑嗔痴,他都已看破。只是任他,也无法预料,有一个旗人少年,会因着自己的死亡,怀念而迷茫。
冥冥之中,那个少年和大师的缘分,或许已终止于取名的那一刻。缘分已中断,羁绊却依旧延绵。少年一日用着那个名字,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仿佛从未断绝,纵使他们从不曾相见,也从不相识。在这场死亡中,少年发现,原来生和死都是那样容易,最艰难的,却是生存的过程。生存了十余年的少年,第一次感到迷惘,他忽然不知道,该去何方寻找生存的意义。
经年累月的骑射,日复一日的淫浸书海,照着父亲所希望的样子前行,他就能够发现人生的意义吗?父亲能够从细节中推断出法璍大师的死亡方式,那是得益于他缜密的头脑、务实的作风和超理性的思维,他能够做到吗?容若茫然了,在得知大师死亡的那一瞬间,占据他内心的,只是凄哀和惘然的柔软。他和父亲,是多么不一样啊,正如同树干上的枝丫,长满诗意的绿叶,却并没有树干的扎实和遒劲。那么,枝叶走上树干的道路,会是最好的抉择吗?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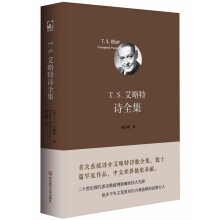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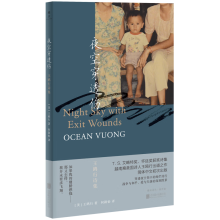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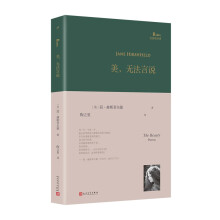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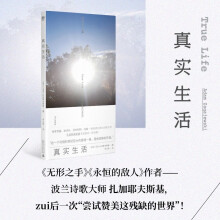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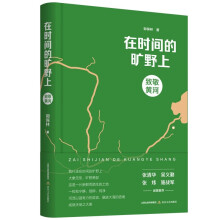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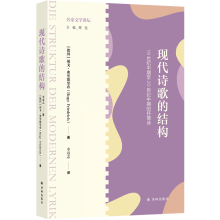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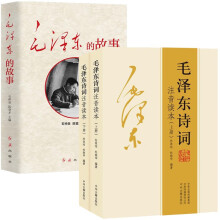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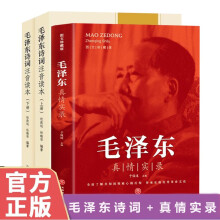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 ——纳兰容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