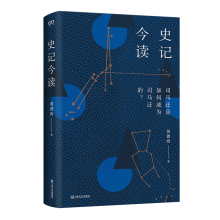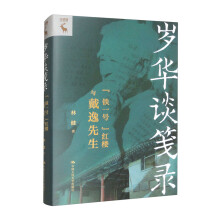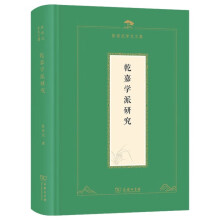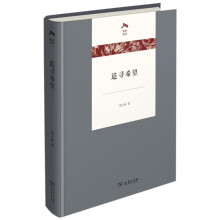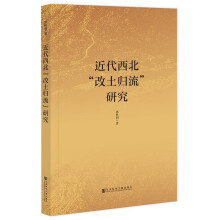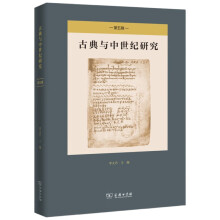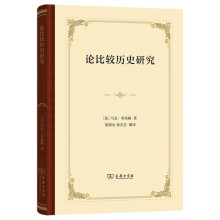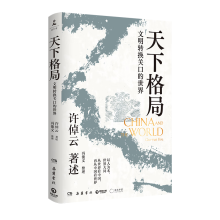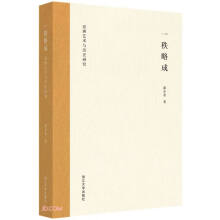《巴金研究丛书:永远的巴金》:
一九四四年,新婚后的巴金同爱妻萧珊先后从贵阳来到了重庆沙坪坝文化生活出版社任职,此时出版社成了作家们聚会的场所,马宗融、靳以是常客,来往最多的还数曹禺。由于战乱,曹禺很穷,有时只能一天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在这种时候,他就会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每次都受到热情的招待。曹禺像敬重巴金那样敬重善良、贤惠、肯把别人困难当作自己困难的萧珊大嫂,曹禺常说:“巴金夫妇对谁都好,他家里每天都有客人,经常有一桌穷客人,虽然那时日子清苦,但只要到巴金家中一聚,心中的忧闷也就消除了。”就是这样,巴金一直如同大哥般地呵护着这位可信赖的小弟。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和曹禺分别定居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此时他们的社会活动也繁忙了起来。每次巴金出访途经北京或赴京参加会议,曹禺总是抽出时间到巴金下榻的房间陪他闲聊叙旧;有时约上老舍、沙汀等老友上馆子点上巴金喜爱的菜肴为巴金接风洗尘;空闲时他们会闲逛北京大街市场,渴了,买上几根冰棒,边吃边逛,十分自在。巴金十分留恋那种轻松随和的气氛,每次都把在北京与曹禺相逢的情景写信告诉爱妻萧珊,在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竟有四十余次谈到与曹禺相会时的情景。
一九六六年六月,巴金和曹禺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作家紧急会议,正当他们以东道主的身份与各国作家以文会友、传播友谊时,一张无形的大网正紧锣密鼓地朝他们头上笼罩而来。当巴金和曹禺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时,就落入了劫难的无底深渊,成了被点名的“重点人物”,被关进了“牛棚”,接着就是抄家、批斗、监督劳动,无休止地写着“交代”。善良、明朗的萧珊没能熬过这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带着人世间的悲愤离开了她心爱的李先生(萧珊对巴金的尊称)和一双儿女。巴金悲痛欲绝,一下苍老了许多。但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仍不忘远在京城也同样遭受厄运的曹禺。巴老的故友之子马绍弥到上海为养母奔丧返京时,巴老托他去探望危难之中的曹禺。马绍弥来到铁狮子胡同三号曹禺住所,只见大院门口张贴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曹禺”的标语,他的家已与世隔绝,后来马绍弥凭着是首钢职工的身份才得以进入那间密不透风的小屋。巴金的问候给绝望中的曹禺心中注入了一泓清泉,人间还有什么比这种纯洁的友谊更加珍贵呢?
粉碎“四人帮”后,曹禺写给巴金的第一封信就谈到:“读了你的《怀念萧珊》的文章,我痛哭不止,想不到她是这样凄凉、孤独地死去。她受了许多罪,她为你受了许多痛苦,你也为她受尽了人世间想不到的苦痛。我想不出你在暮年会遭受这种不可形容的煎熬、苦难。我也想不出萧珊那样坚强,那样的疼你。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又是你真正的好朋友、好妻子……”这也是曹禺对一位他所敬重、一位曾经帮助过他的大嫂迟到的哀悼和思念。
此时,巴金与曹禺虽然都进入了耄耋之年,但他们却感受到了春的阳光。大地开始复苏了,他们又可以重新拿起那支熟悉的笔。巴老要用这支笔夺回被“文革”白白耗费的时间,他要把心中的真话奉献给读者。他拖着病残的躯体,终于在晚年完成了醒世之作《随想录》。他不仅自己写,还不断写信要曹禺多写,他在信中写道:“……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点东西,把你心灵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读者,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擅长写剧本的曹禺深知大哥此时的心情,他告诉巴老:“我正在写个短篇小说;这是遵从你的嘱咐,何时真写出来,也不知。‘六十岁学吹鼓手’本是笑话,如今八十岁写小说,你想,其困难,其可笑,可想而知,但我仍坚持有一点写一点,写一段是一段,总得把它写完,写完了,请你改……”两位老人的心不断地燃烧着,为读者奉献着。
一九八四年,法兰西共和国为表彰在法国被推崇的《家》《寒夜》《憩园》的作者巴金和他著述不倦的精神,以及他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特地授予巴金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和证书,法国前驻华大使马乐专程来驻沪领事馆,代表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举行授勋仪式。那天,曹禺和柯灵应邀作陪。在这庄严的一刻,两位老友站立在巴老的身后微笑着分享着这一殊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