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传人
所有来新罕布什尔寻找
先辈记忆的人聚在一起,
宣布产生了一个理事。
在巴奥,一个乱石散布,农业
凋敝的小镇,斧斤去、杂草生的地方,
思达克这个名字聚拢了那些人。
有人竟然把那里所有
家族的起源追溯到一个
岔路上古老的地窖洞里。
他们从那里发源,人数众多
以至于现在镇里留下的房子
不够住,还得在树林和果园里
这儿一顶那儿一顶地支帐篷。
他们来到巴奥,但这不够:
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留出一天,
围站在那个把他们带到
这世界的坑边,企图探究
过去,从中找出一些陌生感。
但雨破坏了一切。一早天就阴沉不定,
低云拖着尾巴,不时下一阵雨结成雾气。
年轻人之间还怀着希望,
直到快中午,飒飒响的草
确定了风暴的到来。“其他人也在那里
会怎么样,”他们说。“天不会下雨。”
只有一个人从不太远的农场
徒步走来,他没有期待会遇到
别人,就是出于无聊。
一个,还有另一个,是的,有两个人。
第二个是走在崎岖山路上的
一个姑娘。她远远停下来
探查形势,然后做了决定
至少走过去看看他是谁,
也许听一听关于天气的谈论。
这个思达克家的人她不认识。他点头。
“今天没有聚会,”他说。
“看起来是。”
她扫视了一下天空,抬起脚跟要走。
“我只是没事闲逛过来的。”
“我也是闲逛过来的。”
专门给这种互不相识的
亲戚聚会做好的,画在一张
类似护照卡上的世系图,
佩戴者的那一支最详细——
狂热分子绘制的不厌其烦的谱系图。
她猛地把手伸向胸前外衣,
像是要抓住心脏。他们同时笑了起来。
“思达克?”他问。“证明就不必了。”
“是的,思达克。你呢?”
“我也姓思达克。”他掏出护照卡。 “你知道我们即使不是,也肯定是表亲关系:
这小镇到处是姓车希思,娄斯,和贝勒斯的人,
都称许自己身上的思达克性更为纯正。
我妈妈姓兰恩,她可以和地球上
任何人结婚,而她的孩子
还是思达克,今天也肯定来到这里。”
“你拿世系图玩猜谜,
像一个薇奥拉。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妈妈是
好几重的思达克,和我父亲结婚
并不是把我们带回思达克家族的主因。”
“人不能被一个简单的
亲戚关系声明弄糊涂了,
不过你说的事还是让我脑子嗡嗡转。
你拿着我的卡——你看起来很擅长这东西——
看你能不能算出我们的亲戚关系。
为什么不坐在这儿的地窖墙上
把脚伸进覆盆子藤蔓里晃荡?”
“在家族树的庇护下。”
“正是——那样的庇护应该够了。”
“可是挡不了雨。我看就要下雨了。”
“正在下雨。”
“公平地说,没有,只是在起雾。
你觉得这雨看起来是不是能让眼睛清凉?”
情况是这样的:小路
在半山腰屈身向外,
然后在不远处消失不见。
没人从那儿回家。从他们的位置过去
唯一的房子是一个粉碎的荚果壳。
下边隐藏在树丛里的是一条咆哮的溪流,
它的声音对这块地儿而言就是沉默。
他坐着听水声,等着她的评断。
“从父亲一方看起来,我们是——让我看——”
“不要太技术化了。——你有三张卡。”
“四张,你一张,我三张(每一张都是
思达克家族分出的一系,分别都有我这个后代)。”
“你知道一个人和自己关联太紧
会被看作疯子。”
“我也许是疯子。”
“你看起来是,坐在雨中
和从来没见过的我一起研究
族谱。从所有这些关于祖先的骄傲里
我们能得出什么,我们美国佬?
我认为我们都疯了。告诉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被吸引到这个小镇,一个地窖坑穴的周围
就像暴风雨前湖上的野鹅?
我奇怪从这个坑里我们能看到什么。”
“印第安人有一个神话关于奇卡摩刺陀克,
意思是我们从中走出的七个洞穴。 我们思达克族则是从这个坑里挖出来的。”
“你很渊博。这就是你从其中看到的?”
“那么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啊,我看到什么?
首先。我看到覆盆子的藤——”
“哦,如果你要用眼,那么先听听
我看到什么。那是个很小很小的男孩,
苍白、黯淡像阳光下火柴擦出的火苗。
他在地窖里摸索着找果酱,
以为周围是黑暗的,但其实阳光充足。”
“他什么都不是。听着。我这样斜靠着
便能把思达克老祖宗想象的八九不离十,——
他嘴里叼着烟斗,拿着棕色的罐——
保佑你,这不是老爷爷思达克,是老奶奶,
但有烟斗,有烟雾,还有那个罐。
她在找苹果酒,古老的姑娘,她渴了;
让我们希望她找到饮料平安地出来。”
“请给我讲讲她的事。她看起来像我吗?”
“她应该像,不是吗?你是从她而下
那么多分支合起来遗传下来的。我相信
她看起来确实像你。在那儿别动。
鼻子一模一样,下颌也是——
如果允许误差,允许合理误差。”
“你这个可怜的,亲爱的,太、太、太、太奶奶!”
“注意别把她的伟大搞错。别让她掉了辈分。”
“是的,这很重要,虽然你不这样认为。
我不会生气。不过你看我身上全湿了。”
“是啊,你得走了;我们不能永远留在这儿。
不过等着,让我伸手拉你起来。
一颗银色水珠依稀编织在
你的头发上,不会损害你的夏日容貌。
我想拿小溪在空旷的峡谷
所激出的嗓音做个实验。
我们刚看到了幻象——现在求教于声音。
这肯定是我小时候坐火车的时候
学到的。我那时经常把那啸声
当作从它身躯内部说出的声音。
不管那是说还是唱,或乐队在演奏。
也许你具备我所说的那个本领。
我从来没有在小溪如此狂野
下降所发出的轰鸣声里倾听。
它应该会给出一个更清晰的预言。”
“这就像你把一个图像投射到屏幕上:
它所有的意义都出自于你;
那些声音给你的是你愿听到的东西。”
“奇怪的是,那是他们愿给出的任何东西。”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肯定很奇怪。
我想这是不是你自己的虚构。
你认为你今天会听到些什么?” “从刚才我们一直在一起的事实——
不过为什么在我会听到什么这个问题上花时间?
我要告诉你那些声音真正说的是什么。
你就待在你在的地方不动
再待一会儿。我不能有太仓促的感觉,
否则我就无法进入,听到那些声音。”
“你是在进入某种恍惚出神状态吗?”
“你必须非常安静;不能说话。”
“我会屏住呼吸。”
“那些声音似乎在说——”
“我在等。”
“别!那些声音似乎在说:
管她叫瑙西卡,她不害怕
冒险结识的那个人。”
“我就让你那么说吧——经过考虑之后。”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阻止。
你要的是真实。我不过是用那些声音说了出来。
你看他们清楚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虽然我们之间名字有什么要紧——”
“我可否以为——”
“好好儿听。那些声音说:
她叫瑙西卡,从地窖的
覆盆子间找出一根你会发现的
熏黑的木料,砍削成
门槛或其他边角料
用来在这老地点建一所新房子。
生命还没有完全从它消失。
请来吧,把这里当作你的夏日居所,
也许她会来,仍旧无所恐惧,
在敞开的门口坐在你前面
膝上放着花,直到枯萎,
但却没有跨进那道神圣的门槛——”
“我很好奇你的预言往哪儿发展。
你知道它有点不太对,
否则就应该用方言说。你想用
什么人的嗓音?肯定不是老爷爷的
当然也不是老奶奶的。唤起他们中的一个吧。
在这地方他们最有权利被听到。”
“你似乎太偏爱我们的太奶奶
(去掉了九个太。纠正我如果我搞错了。)
你将很可能把她所说的任何东西
都当作是神圣的。但我警告你,
在她的时代,人们说话是朴实的。
你觉得你还想在这样的时刻把她招来吗?”
“我们随时可以把她从话题里去掉。”
“好的,现在奶奶说话了:‘我不知道!
也许我这样看问题不对。
但现在这些人怎么比得上过去的人,
将来也不会有人符合我的想法。
虽然一个人不能对新来者太苛刻, 但他们太多了,怎么安慰得过来。
如果我能看到更多腌他们的盐
我会感觉好点儿。
孩子,照我说的去做!你去拿那根木头——
它还和当初刚砍下时一样好一
从头开始——’就在这儿,她最好停下。
你能看得出什么在烦老奶奶。
难道你不认为有时候我们把老一辈
翻炒过头了吗?重要的是那些理想,
它们还保留着某些现实的相关性。”
“我能看得出我们将要成为好朋友。”
“我喜欢你说‘将要’。你刚才说
天将要下雨。”
“我知道,它在下雨。
我让你说了所有那些。但我现在必须走了。”
“你让我说的?深思熟虑?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样说再见?”
“是啊怎么样?”
“你能不能把路留给我?”
“不,我不信任你的眼睛。你说得够多了。
现在把你的手伸出来。——摘给我那朵花。”
“下次我们在哪儿见面?”
“除了这儿
我们还有哪里再见,在我们相会于别处之前。”
“在雨中?”
“必须在雨中。在雨中的某个时刻。
明天的雨里,如果下雨,我们就相见,可以吗?
但如果必须,阳光下也行。”就这样她走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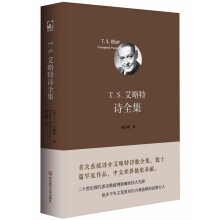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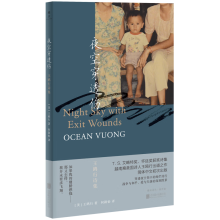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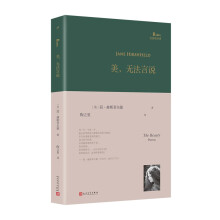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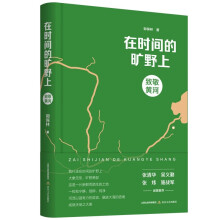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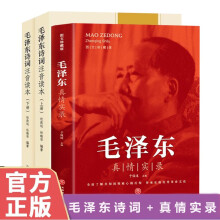
——T.S.艾略特
★弗罗斯特是美国第一位堪比世界水准的的大师级诗人。
——罗伯特·格雷福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