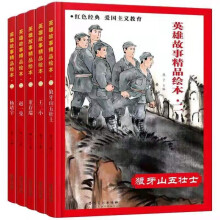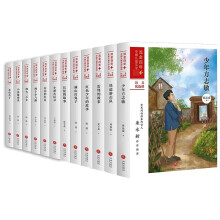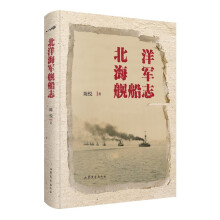《正面战场·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当江兴轮开出三小时后,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接到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密电:在汉口日本租界设置的六门高射炮,与所存五百箱弹药,须在该部撤退时抢运后移,倘有贻误以军法追究。司令部再没有船只可以载负,于是急电江兴轮转舵回汉。当江兴轮转回汉口时,已是深夜十时半了。江兴轮虽没有装载重要物资,乘客却有一万多人,高射炮无法下舱,只得安置在船面。启碇时已是二十五日清晨三时许,从武昌珞珈山东面,传来稀疏的枪声,这时,司令部的建兴轮领先,江兴轮随后,离开了武汉。建兴轮小而快,可以不择水线直航前进,而江兴轮是江轮,必须按照曲线水槽进发。行驶至新堤江面时,建兴轮已将江兴轮抛到后面四十多华里了。在建兴轮领先前进中,曾遇到几次敌机,由于船面掩蔽工事好,舵工也很有经验,都闪避过去了。大家只为江兴轮担心。建兴轮驶到小新镇,追上了先一天军委会侍从室开出的建武轮。建武轮在开出的当天,遭敌机扫射,死伤了十余人,连陈布雷秘书长站在锅炉旁,身穿的猪皮袍子也被子弹打穿了几个洞,幸而没有受伤。
据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一年中与敌人在水上运输的斗争经验,长江上下船只一离开武汉约四五十里,随时都可遇到敌人的水上飞机,总是两架一队。敌机一遇到船只就猛烈扫射,接着是一架凌空监视,一架降低或落在水面与船只平行,打着手势,表示要察看。
并且喊出结结巴巴的中国话:“你的国军?你的武器?你的老百姓?”飞行员不一定每人都会说这几句话,但总的不出这几句话的范围。我们的船只总是用篷布围盖得很严密,人员物品都落舱,上面放些不重要的物品作掩护。一听到飞行员喊话时,押运人员即便衣出来,揭开篷布一角,或做手势,或答话。在船的篷布上张贴老百姓回乡的标志,也算是种掩护。再就是由船工放三声汽笛,以表示敬意,但当时的船工一般都拒绝使用汽笛。这三种对敌方法被当时的管理员们叫做“文昭关”;敌机如果发现船上有穿军服的人,就疯狂地扫射,管理员们叫做“武昭关”。
当时江兴轮篷顶上都是杂色军民乘客。我们在建武轮上的人都很担心,正在议论的时候,引水员很紧张地走进底舱来说:“江兴轮离我们水程六十余里,旱道不过二十里。前一小时,敌机两架飞过去后,我们听到过枪声。后来看到敌机向梁子湖方向窜去,一架好像受伤落下,一架直接向东飞去。约三十分钟后,又来了六架飞机,顿时水上传来了沉重的轰鸣声,可能是江兴轮遇险了。”副司令庄达即嘱咐三个船舶管理员与一个水手,携带款项,雇上轻快小木船,限于当日抵达肇事地点查勘,办理善后,并须在三日内由陆路赶到沙市会合。
二十九日晚,建兴轮转进宜昌时,那四位去侦察江兴轮出事的人员回来了。报告的情况与引水员所预料的并无不同。只不过证明:遇险地点,江面很宽,江滩极阔,南岸村庄离江心最近处约有十二三里,当地老百姓听到轮船遇险的轰鸣声,赶到江边时,江中业已平静,看不到船只了。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根据事前事后经过情况,以及二十六日在新堤江面遇险隋况呈报参谋总部备核。
呈报一个月后,原乘江兴轮遇难脱险的船舶管理所书记李世芳回来说:“当日机两架发现江兴轮上有军人时就开始射击,死伤很重。飞行员随即打手势,强迫折转汉口。船上的高射炮手抑制不住怒火,就开炮射击,一架敌机受伤,逃到武昌西南面落下了,一架向东逃跑了。这时,我们司令部还有三个管理员也是随船撤退的,主张将船开足马力,搁在浅滩上,大家涉水登陆,以防敌机再来报复。但人员太多,命令传不下去,尤其是高射炮队的官兵,认为敌人水上飞机数量不多,也没有战斗力,不敢再来。倘若再来,可用高射炮与步枪反击,定能击退敌机,比涉水登陆损失小。他们一面说一面架设高射炮。可是船上人多,船面地位也有限,仓促之间,一架高射炮的位置还没有摆好,敌机六架,已凌上空,投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炸弹与燃烧弹。顿时船尾、中舱中弹燃烧,船尾开始下沉。船上秩序大乱,号哭声、救命声、爆炸声混为一团,高射炮手受了伤,无法抵抗,高射炮队的官兵都在血水中沉没了。我住在三楼边舱,先用绷带连着我的妻子与最小的孩子,让他们跳下去,我左右两手抱着两个大孩子也跟着跳下江中。一浪卷来,我的妻子沉没了,我喝了水,两手一松,两个孩子不知去向。我因穿着棉袄就漂在水上,直到漂离遇险地点约六十里才被渔民救起,到第二天中午我才苏醒。后来我在那里休养了五天,得悉那里叫新泽口,是回水地带。船只出事后,漂流的人,过此没有办法搭救。在那些天里,我也了解到江兴轮出事后,一共救了八十四人,其余连我们的三个管理员在内一共一万多人都死了。”李管理员的血泪控诉变成了愤怒的呜咽,引起了大家同仇敌忾的决心!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自十月二十四日撤离汉口后,对保卫武汉的运输任务即告一段落。我们转进到宜昌已是十一月一日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