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亲缘关系的确还经常提供一种稳固的温暖或亲密的关系网络,它持续地存在于时间一空间之中。总体来说,亲缘关系所提供的,是一系列可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既在原则上也(常常)在实践上建构起了组织信任关系的中介。
关于地域性社区,也同样有许多类似的东西值得一谈。这里我们应当避免把社区浪漫化的观点,而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作比较的时候,这种浪漫化经常浮现在社会分析的表面。我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想要强调以地点(place)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地域化关系的重要性,而这时地点本身还没有被伸延了的时一空关系所转变。在绝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包括在大多数城市中,地域色彩浓烈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场所,它在空间上的低度伸延支撑着时间上的高度凝固。在前现代时期,迁移、游牧以及商人、冒险家长距离的奔波是较为平常的事。但是同现代交通工具所提供的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以及普遍意识到的其他生活方式)比较起来,前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于相对凝固和隔绝状态。前现代情境中的地域性既是本体性安全的焦点,也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构成,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种地域化的本体性安全实际上已经被消解掉了。
第三种影响是宗教宇宙观的。宗教信仰可以成为极端焦虑或绝望的源泉之一,其如此之重要以至于不得不被看作是许多前现代环境中(人们所经历的)风险和危险的主要参数之一。但是,在其他方面,宗教宇宙观却在伦理与实践方面提供了对个人和社会生活(以及还有对自然界)的解释,这些解释向信仰者们所描绘的,是令人感到安全的环境。基督教对我们的神令是:“信仰我吧,因为我是唯一真正的上帝。”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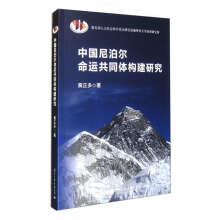





——赫伯特·林登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