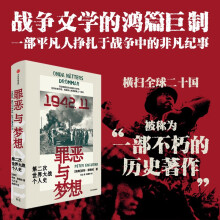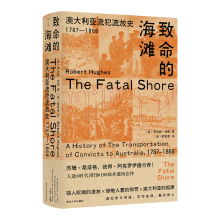《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03:法国的沦陷》:
在大战方酣的时刻组织内阁,尤其是一个联合内阁,大概比在和平时期容易得多。责任感压倒一切,个人的打算也就退居其次了。把主要的安排同其他各党的领袖们——在各自的组织正式授权下——确定以后,所有我邀请的人,就像作战中的士兵一样,都毫无异议地表示要即刻走向指定给他们的岗位。把政党的基础正式确定后,据我看,在我所要会见的大批人士中,任何人都未抱有私心。即使少数几个人有所犹豫,那也还是为公考虑。这种崇高的行为在保守党和全国自由党的许多大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职位,抛弃自己的事业,而且要在这重大关头和令人激动的时刻脱离公职,有许多人甚至是终身脱离。
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一百二十余席。张伯伦先生是他们推选的领袖。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必然了解,我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或实际斗争中度过的;我曾经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他们分道扬镳,后来,又作为财政大臣回来与他们共事。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在关于印度、外交政策和缺乏战争准备这些问题上,我是他们主要的对手。接受我当首相,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许多可敬的人感到痛苦。而且,忠于党所推选的领袖,是保守党人首要的特色。如果说在战前的几年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未能履行他们对国家的责任,那也是由于他们忠于他们所选的领袖的缘故。这些考虑丝毫没有使我感到担忧。我知道,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
首先,我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下院的领袖兼枢密院长,他都一一接受了。这件事并未宣布。艾德礼先生告诉我,在这样的安排下,工党不容易工作。在联合政府中,下院的领袖必须是大家都接受的人。我把这点告诉了张伯伦先生,在他爽快的同意下,我亲自担任下院领袖,一直到1942年2月。在这个时期内,艾德礼先生担任我的副职,处理日常工作。他在反对党中的长期经验是有很大价值的。我只在有最严重的事情时才到场。这样的情况是经常有的。许多保守党党员觉得:他们党的领袖没有被人看在眼里。每个人都敬佩他的为人。当他以新的身份第一次步人下院时(5月13日),他的党的所有党员——下院中的大多数人——一致起立,对他热烈地表示同情和敬意。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向我致意的主要来自工党议员席。不过,张伯伦先生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目前并不是排斥那些长期担任要职的有才干的爱国人士的时候。如果这些爱好批评的人想怎么就怎么的话,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三分之一就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先生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而且,我也无需研究所有这些罪责是不是应由一方来承担。正式的责任是应由当时的政府承担的,但是道义上的责任则牵连甚广。可以摘引工党大臣——自由党大臣也不例外——所发表的许许多多言论和投票记录,他们的那些言论和投票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愚蠢的,这在我脑子里都记得,而且可以详细列举。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不追究过去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些分裂的倾向进行了抵制。我在几星期以后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的迫害异端的人们。
5月11日清晨,我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我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当作我的临时总部。我向他报告我同艾德礼先生的谈话和组织新政府的进展情形。“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须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十一号的旧居,并且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我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在晚间12时50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察看地图,进行商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