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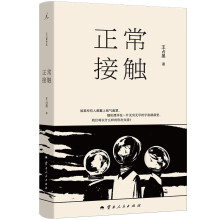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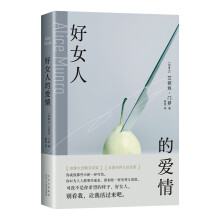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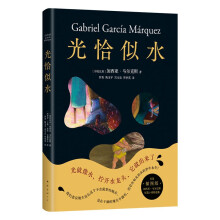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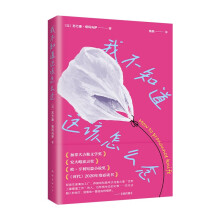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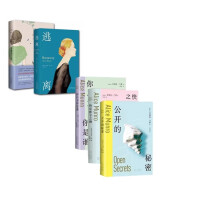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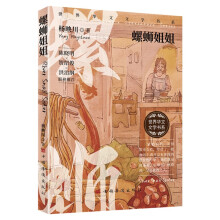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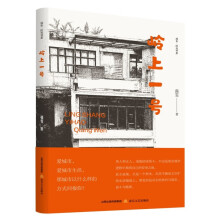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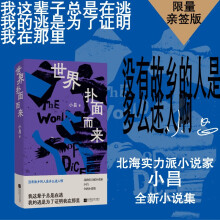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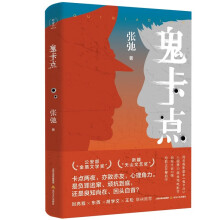
当推理小说不仅是推理小说,当导读不仅是导读
劳伦斯·;布洛克、约瑟芬·;铁伊、东尼·;席勒曼全赖唐诺一双慧眼引介到华文世界
侯孝贤、王家卫、梁朝伟、朱天文多因唐诺一支健笔成为劳伦斯·;布洛克的粉丝
这个他妈的都市丛林臭滥污里有什么,你可知道?有八百万种死法。
39篇唐诺所作劳伦斯?布洛克作品导读首次全收录
《黑暗之刺》
他死的时候,我正在做什么?
十九世纪德国大史学家德洛伊森以为,已经发生的事并不自动成为“历史”,除非它跟我们的“此时此刻”有了某种牵连,生出了某种意义,被我们重新记忆、思索、组织,并认真地理解。
那,已经发生了九年之久的一桩谋杀案呢?芭芭拉·爱丁格原来一直被当成一名冰锥疯子凶手的一长串倒霉受害者之一罢了,然而九年之后,凶手偶然落网,很光棍地坦承一切罪行,独独坚持芭芭拉不是他杀的。因为案发当时他人在牢里。此外,芭芭拉的死法也确实和其他死者有些许出入,很像,但有出入。
于是,已经安心甚至已经停止哀伤的芭芭拉父亲重又“生出意义”,他要找回这段历史,要重问为什么有人残害他这个毕业于韦斯利女子学院(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念的贵族学校)的好女儿,然而,对官僚系统的警方而言,这些只算构成疑义,尚不足以生出大张旗鼓重开调查的意义,于是,案子遂辗转来到我们这位“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自由工作者斯卡德先生手上——再次证明,公营单位只能做例行性的简单工作,困难的,只有民间自己才有机会完成。
斯卡德的警言是: 你可能白花钱得不到任何结果;你可能真找到凶手是谁,但证据湮灭再无法有效把案子送上法庭;更可怕的是,“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自己说的——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不知道那个理由,你可能活得快乐一点”。
A Stab in the Dark,黑暗之刺,指的是冰锥杀手的杀人习惯——用冰锥刺穿被害人双眼,因为他害怕自己杀人的最后影像留存在被害人的视网膜,或可被某种科学仪器解读出来;也指的是斯卡德匕首一般重新刺入九年前的黑暗时光隧道和幽黯人心之中。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你看起来像见到鬼,不,我说错了,你看起来好像找鬼一样。”——这是暌隔九年之后,斯卡德重新回到芭芭拉被杀的公寓房间,当前的女房客脱口而出的骇异之语。
当然,我们的谋杀历史学家斯卡德先生完全了解,九年,对一个籍籍无名的谋杀被害者是什么意思,这可不是地质学——九年对地质学而言短得毫无意义,它几乎形成不了任何可察觉的变化,事后它又躲在碳同位素测定的误差之中,毫无法子把它给叫出来——这是现实人生,基本上,它占到我们人寿几何达八分之一的比例,可发生很多事,也可湮灭很多事,您要不要自己现在就试试,先回忆一下,九年前的此时此刻您人在哪里?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再试着猜一下,九年后的此时此刻,您人又可能在哪里?可能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事实上,九年时光,不仅有形的事物变了,甚至就连记忆也不一定可信了——斯卡德对此知之甚详,他的说法是,“回忆是一种合作的动物,很愿意讨好,供应不及时,常常可以就地发明一个,再小心翼翼地去填满空白”。
因此,来路已蓝缕,去处不可知——九年前的谋杀现场,对斯卡德而言,只可能存在着“感受”,不可能有“线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在我个人有限的侦探小说阅读经验之中,斯卡德的办案方式可能是所有可见的神探名探私探妙探中最“没效率”的一个。斯卡德自己常讲,他只是尽可能到处走走看看问问罢了,没特定目标或理由。他心知肚明,百分之九十五走来看来问来的资讯和想法完全没用,真正你破案要的只是剩下那百分之五,然而,你无从得知这有用的百分之五何时出现,说穿了你也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哪个部分的百分之五。
这很像我们说放射性铀原子衰退为铅原子,科学家只晓得一定时间内(如半衰期)一定比例的铀原子会转化成铅原子,但我们永远无法事先确定哪颗变哪颗不变,其间全凭几率,或俗称运气。
然则,那百分之九十五对办案而言,彻底浪费掉的行走、问话和感受,我们能拿它干什么呢?
感谢上帝,有这么多“浪费”,作为一个读者,我得说,这些之于直接破案如敝屣如垃圾的破碎片段,一直是阅读时的真正珍宝,是最好看动人的所在,它们闪闪发光四下散落着,拉开传统侦探小说只盯紧罪案的(略呈)线性狭隘视野,让小说中的世界有了现实的光影反差,也让原本“概念化”的小说棋子式人物,一个个饱满地站了起来。
举个例子好了。斯卡德探案的另一部小说《刀锋之先》,他受托找寻一个来到纽约不久便告失踪的年轻女孩,寻访之中,他脑中一直想的是,“她这么寂寞,能到哪里去呢?”——这是负 责翻译此书的林大容小姐跟我讲的,她译到此句时浑身起了生理变化,事后叙述仍动容不已。
或者如《黑暗之刺》这本书中,斯卡德也严重地怀疑凶手是芭芭拉那名拈花惹草的事后再婚丈夫,但他想的不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我也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可能杀人”,而是,“结婚的人经常会互相谋杀,有时候他们需要花上五年十年才做得成这件事”。
这很显然都和效率无关,要看效率,那我们顶好回到古典推理世界,回到那些异于正常人的神探身边去——甚至像福尔摩斯,效率高到只一眼就瞧出来人是海员或会计,有没有到过中国或一度富裕近况潦倒云云。斯卡德没这本事,他只是踽踽徐行于大纽约市的普通人罢了。
……
马修·斯卡德系列
《父之罪》上床·作为一种志业
《在死亡之中》从斯卡德的十月之旅讲起
《谋杀与创造之时》向困难处去
《黑暗之刺》他死的时候,我正在做什么?
《八百万种死法》潘多拉的盒子
《酒店关门之后》酒店关门我就走——走哪儿去?
《刀锋之先》献祭的花
《到坟场的车票》系好安全带,我们要起飞了
《屠宰场之舞》我是个神,我无力自拔……
《行过死荫之地》日已西夕·笑话远矣
《恶魔预知死亡》不自由·毋宁逃
《一长串的死者》小说,像一只小鸟
《向邪恶追索》鉴赏布洛克
《每个人都死了》行走的城市
《死亡的渴望》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繁花将尽》斯卡德死亡曲线
《烈酒一滴》祭神如神在
《蝙蝠侠的帮手:马修·斯卡德短篇探案》今夜没有人死掉!
雅贼系列
《别无选择的贼》贼的世界
《衣柜里的贼》锁——罗登巴尔世界的必要之恶
《喜欢引用吉卜林的贼》有关吉卜林
《阅读斯宾诺莎的贼》如果石头有知觉……
《画风像蒙德里安的贼》从莫奈到罗登巴尔
《交易泰德·威廉姆斯的贼》一则魔咒·暨一位神经质的屠龙勇士
《自以为是汉弗莱·鲍嘉的贼》梦境的入口
《图书馆里的贼》这个世界不配拥有像你这么美丽的人
《麦田贼手》这一代
《伺机下手的贼》说给我们听吧!
伊凡·谭纳系列
《睡不着的密探》先有地图的冒险旅行
《作废的捷克人》原来有这么神奇的化妆术
《谭纳的十二体操金钗》加法的冒险故事
《谭纳的非常泰冒险》逃走的英雄
《谭纳的两只老虎》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杀手系列
《杀手》关于杀手凯勒
《黑名单》航向偶然的大海
《杀人排行榜》走向乞力马扎罗山的大象
非系列
《小城》这些人与那些人
《骗子的游戏》有一只名叫劳伦斯·布洛克的蝴蝶
《布洛克的小说学堂》书写的技艺之路
温馨提示:请使用惠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唐诺对劳伦斯·布洛克所花的力气应该是最大的。可以说,对布洛克的喜好以及认为对于他的推荐应该单纯的推理小说范畴的观点。
——詹宏志
虽然这个书里面看起来,唐诺是一个颇为被动的写作者,他就是不得已扮演了出版的角色,然后在出版社的要求之下,必须要为这些他推出的推理小说做一个导读的工作,可是你可以看到唐诺在做这个写作的时候,他自己非常地自得其乐,其中写了很多他身边发生的事情、他的价值观的推演过程,那这些都是我认为好作家必须要具备的特质---就是他得乐在其中,他得在写的时候觉得很得意,有迫切感要告诉你这一些事。我常常在帮人家导读的人的书里面,看到一些过度冷静或者过度理性的写法,相对来讲,唐诺的写法是充满了乐趣,让人即使对于推理小说毫无兴趣,纯粹看一个人怎么样表演他在阅读推理小说这件事情,唐诺的书都可以满足地看到这种表演。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唐诺作为一个作者,他能够用我们很少看到的有趣活泼的或者带一点辛辣讽刺的轻蔑态度,来解释一些在台湾常常被忽略的一些概念,这些都是在一些高傲的知识分子写书的时候,常常没有办法得到的一种优待。我觉得在看唐诺写推理小说的时候,能够因此吸收到非常多……老实说跟推理未必那么有关的想法,一些历史上的演化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支线的知识,这些都是阅读的乐趣。如果你是希望很有效率地吸收推理小说的简介,我觉得唐诺的书未必是首选,可是如果你要读一本有趣,然后可以遍及地去培养出非常精确而且标准比较高的对文学的鉴赏能力,我觉得唐诺做了一次非常好的示范。我们作读书节目的人,当然对于其他爱读书的人,也都会有一份亲切感,尤其是看到一个爱读书、会读书,而且能够把那个感觉传递的特别的准确而清楚的人也会很兴奋,这就是特别为你推荐唐诺的书,尤其这两本他对推理小说的导读。
——蔡康永
唐诺的文字就是会有读起来畅快的感受,更不论那些大快人心,我也这么想却无法表达的那些,却被精确整理出来的认同。
——陈绮贞
唐诺的“强项”不在记忆力,而在谈天说地的“随意性”,尽管叙说主线不离书、阅读与写作,也谈时政,但惟其娓娓道来的恬淡,才深具震撼力,才能谈出创意与精彩,道出真理。
——《亚洲周刊》
詹宏志跟唐诺不仅是台湾1990年代推理小说翻译出版的重要推手,唐诺更曾经化名马波,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具后设意味、大量挪用克莉丝蒂典故的《芥末黄杀人事件》。因为这些作家的积极参与,促成纯文学与大众推理文学场域之间更多元的互动与交流。
——陈国伟
我一直觉得布洛克小说最好看的相当一部分,便在于他写的纽约,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让所有他笔下的死亡在无比的华丽和无比的险刻凶残之间穿梭而行…也亏得有纽约这么个城市来支撑,这样的死亡才成立、才说得通,不至于轻飘飘的一吹就走,犹能如当年的汉密特和钱德勒一般,铁钉般又深又牢地打进读小说的人心里。
——唐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