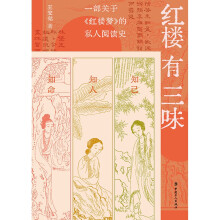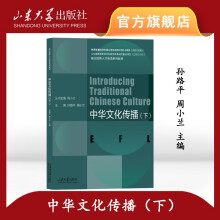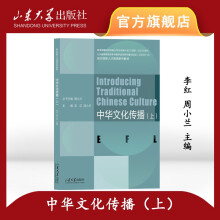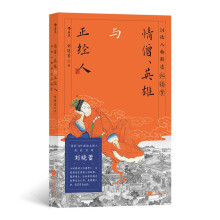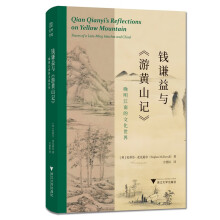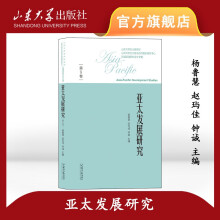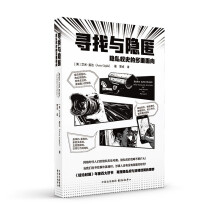第三节大学师生关系
大学师生关系为何物,如梅贻琦所言:“从师受业,谓之从游。”[34]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的师生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试选择若干过去大学师生交往的一些小片段,从中可以感受到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一些特质。营造温馨之校园,校长甘当师生情感的支持之源。所谓营造民主温馨之校园,就是把学校视为一个大家庭来加以维系和建设。大学校长中既是卓越的管理者、治校者,又是优秀的教育家。但展示其治校风格,言行举止不一定都是刻板或威严。实际上,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文化这些抽象名词。反映到具体学原民国大学与台湾“复校”大学对接比较研究校身上,其实就是看这所学校是否具有民主办学、爱护师生之类的小特征;而大学特色、个性则隐匿在这些细节中,并由此引领其生成优秀的校园文化。燕京大学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校长办公室,反映自己认为是必须找司徒雷登反映的问题;司徒本人更是经常在自己住所举行各种师生亲善联谊活动。”[35]1927年,司徒雷登在《燕大月刊》发表一篇文章,抒发了他对师生的情感:燕大目前的情形,是十分乐观的;在学生人数和质的方面,可以乐观;在一种无上的友爱和忠诚的精神,充满着燕大教职员与学生之间,这方面看更可以乐观。[36]金陵大学则把学校灵魂即精神的铸就放在首位,其校长陈裕光认为“盖现今之大学教育为一躯壳,而精神则为其灵魂”。他为金大描述的精神气质是诚、真、勤、仁,在此精神的感召下,金大校风纯朴,“诚心向学”的人最受尊敬,不无学术的人则很难有立足之地。学习、生活在金大的校园中,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校长之间,人际关系都很融洽,“师生老幼,休戚相关,苦乐与共”,教师是“经师”,也是“人师”,为人师表,上行下效,仁民爱物,蔚然成风。[37]作为金大公认之充满仁爱精神的校长,陈裕光待生如子,即使与他政治立场对立的学生,他也尽力保护。1947年“五二○”学运后,当局拟定名单准备进行大拘捕,陈裕光闻讯后,迅速采取措施,将问题学生保护起来,结果是这些学生不仅没有被捕,也没有被开除。优良的校风与校园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总会潜移默化并实实在在地作用于每一个教师与学生,并在他们身上打上烙印。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认为:“教育氛围绝不限于书本教育和知识教育,而应注重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为此,他注重通过校园文化与各种校园活动来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热爱集体、热爱公共事业、一心为公的思想。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使南开学校的风气非常优良,学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南开的学生特色也由此呈现出来。[38]近代哲人布勃(MartinBuber)说:“真正配称为教育的,主要是品性的教育。”而如何协助年轻人形成良好品性则是教育者最大之任务。[39]品性之培养,与校长的率先垂范是密不可分的。上述这几个只言片语之小片段,说明校长的民主作风,不仅可以让师生一体,共同践行其教育理念;同时,校长本身若借助其“身份”对学生施放被爱的感染力,同样亦能达至影响学生品性甚至价值观形成的目标。中国著名教育家赵紫宸,1904年入东吴大学预备科,当时最困扰他的是“怕入了邪教”。东吴学习初期,赵相信“中国自有文明,西洋宗教,既为迷信,更非所需,岂容染我中华净土。”
故对于班中热心传教之同学,赵更当面直斥,被同学冠以“急先锋”之名,遂为非宗教运动的小健儿。他形容这是爱国心与排教心浑杂的经验。而促成赵彻底改变其信仰的则是一次师生聚会,赵向东吴大学首任校长孙乐文(D.L.Anderson)请益,孙特吩赵曰:“紫宸,我看你乃一深思的青年,你当自思。”赵晚上回到卧室后,想及“我是一个深思的青年,孙先生知我也,士为知者死可矣。”校长的知遇之厚,加上东吴老师对学生的宽容与友善态度,他便领洗成为基督徒。[41]这个案例也从侧面说明,校长扮演师生情感之源的角色,其实就是在示范演绎其的教育理念与个人操守。
教师热爱学生,学生亲其师、信其道。明代教育家王守仁曾指出师生关系应该和谐自如,要充满师爱,学生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因此教师应带头“责善”。梅贻琦校长对学生充满热爱,他说:“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也是我的学生。”著名数学家杨武之先生看上去严厉近乎古板,但绝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一生对他所教过的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他的许多学生,后来的成就也许比他更大,可杨先生一丝不苟的为人,给他们一生的影响却无法估量。[42]在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上课时,常戴一顶呢帽。
每至学年伊始,给新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老师对学生的尊重,细致于此。在一个如此充满师爱与被尊重的和谐氛围中,学生自然会亲其师而信其道。另外,民国时期学潮迭起,故分析大学教授对学潮的态度,是一件值得深思的话题。尽管他们当中的政治主张并不一致,有所谓左右派,或偏左偏右之分,不少人也并不赞成学生过多参与学运而耽搁学业。“我对于学生远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蔡元培文: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傅斯年也曾说:“我们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即热衷政治活动,尤其是上街游行),英语永远学不好。”不仅是教授,即使于部分学生中,对同学过多参与学潮也同样持否定态度:“一位叫黄迪的学生,他用两年的时间专研中国的学潮。据他的统计,每次风潮发生时间,百分之九十多是在学期考试前两三个星期以内;每次学潮,意识的和非意识的,都含有避免学期考试的心理作用在内。”[44]
但在对学生因参与学潮而可能受到当局的伤害时,教授们往往会挺身而出,站在学生一边,充当学生的坚定保护者,从而显示出浓浓的疼生之情。1947年5月20日,王铁崖、向达、沈从文、周作仁、俞平伯等31位北大教授,联名在《观察》发表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向政府表达他们对学潮的态度:“青年学生的心灵原是非常纯洁,其对国家的前途亦最为关切。以往如辛亥革命,如国民革命军北划,如八年抗战,无一次不有青年学生参加,也无一次青年学生不尽他们最大的责任。目前各地青年学生之反内战,反饥饿,以及要求教育改革的运动,纯如胡适校长沉痛的表示,纯是由于不满政治现状……今日内战愈演愈烈,青年学生所呐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了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应当同情……希望政府对于青年学生的运动予了解和同情。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状,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推诿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殷鉴不远,不敢不告。”[45]
1948年5月,针对当时国民党北平主委吴铸人在举办总理纪念周大会上,发言称学潮多为“暗受奸匪利用”之类,引起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90位教授的不满,联名公开发声表达对当局的抗议。他们说:“学潮发生固属不幸,但接连地伤害学生,包围学校捣毁校舍等暴行,当局实不能辞刺激学生之责。手无寸铁的善良纯洁青年对于这样假藉暴行来挑衅的手段,表示愤慨与抗议,我们只有衷心同情。为了维护学府尊严与争取安全保障,我们也会忍痛罢教,唤起全国人士的注意,借以制止层出不穷的迫害与惨案,挽回迭受摧残的教育生机。目下学潮正在渐起平息中,而党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极尽挑拨、诬蔑、威胁之能事,用心何在,令人诧异。”[46]中国史学会原会长戴逸回忆自己在北大学习阶段,曾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捕,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将他“保”出来的。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他颇得胡适赏识,但胡适坚决反对他参加学生运动,劝他要好好学习,不要参加这些学生运动。他回忆说:“我跟他顶起来,他很不高兴。”由于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且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戴逸因此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全国通缉。当他被捕后,胡适并未因他不听自己话、甚至顶撞自己惹自己不高兴而不管不问,更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为救他出狱,“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胡适忙写了一封信,跟他们厅长说,这是个好学生、优秀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
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所以我在被审了两个多钟头后就被保释出来了。”[47]对这种师生之情,无须多言了。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师生关系民主和谐。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相当重视学生的自治。为了养成学生自律的习惯,蔡先生一反以往的做法,不再公布学生的学习成绩,以消除学生的功利思想,使他们自觉为学问而学问,而不是为成绩而求学。[48]西南联大高高举起“通才教育”的旗帜。对学生实行学分制,规定每个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即可毕业。同时还实行了选课制,学生有选择课程和老师的自由。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教师将会竭尽全力上好自己的每一次课。不仅学生有学习的自由,老师讲课也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49]学术自由、通才教育的大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大学师生潜心向学的精神以及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大学师生关系民主和谐。联大毕业生,已故数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曾回忆说:“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50]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