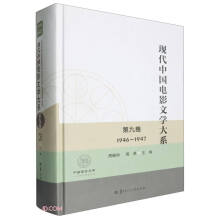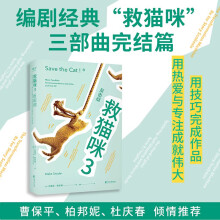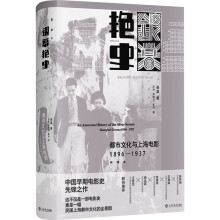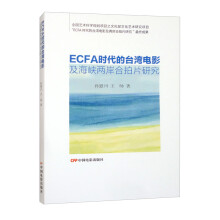《从外来杂耍到本土影业:中国电影发生史研究(1897-1921)》:
三 华人观众:时局的焦虑与赏玩的快感
除了中间短暂地在张园安垲地大洋房表演过一两次之外,赫兹的主要演出场所是兰心大戏院。兰心的主顾以西人居多,但依然向中国观众开放售票。而前往观看的中国人,大多应并非底层民众,至少是有一定经济能力和文化修养的文人和官员。①其中甚至不乏地位显赫者——时任四川总督的裕禄就曾和家人、随从一道出现在兰心的包厢中。②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则中国观众对赫兹所放映电影的观感和英侨观众之间判然有别,这一点可以从《申报》的评论文字中看出来。《申报》是英商美查(ErnestMajor)等创办于1872年的一份中文报纸,面向的读者是华人群体,美查很少过问具体的编撰事务。因其全面、真实,《申报》成为上海报纸的代表,在市民心中有很高的权威性,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因此它对赫兹的表演和放映的报道,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观众的重要材料。
1898年5-6月间,《申报》上发表了四篇有关赫兹演出的报道。和《北华捷报》一样,这些报道称赞了赫兹出神入化的表演;而对电影的观感则要简单得多,主要停留在场面的描摹上。比如,在赫兹放映《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六十周年庆典》的那一周里,《申报》记者对电影的记忆却是:“所演影戏多出,类皆生趣飞动,形状逼真,而亦以二出为最异。一为试演水雷,汪洋大海,波涛万顷,初望之风迥绮觳,鞯纹荡漾,俄而大声发于水上,洪涛飞溅,直薄层霄。二为车士,如出队状,有无数马兵步兵,整队而出,疾徐进退,接踵前行,观之逾时,未见其尽,不啻有千军万马,行乎黄沙白草间也,技至此可谓神矣。”在这篇印象记里,让英侨观众激动万分的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庆典影片,被漫不经心地忽略不计了。原因自然很有可能在于赫兹放映电影的时候没有任何中文讲解,中国观众无从辨认出女王的形象;而即便能够辨认出,这一形象所引起的也绝不会是民族自豪感,而更有可能是痛彻的被殖民的记忆,以及丧失国家主权和国际地位所带来的羞辱、愤怒、悲哀、恐惧等负面情感。而和1897年库克等放映的时候一样,“试演水雷”和“车士出队”这两部和军事有关的影片被视为当晚所演中最优秀的两出。之所以如此,恐怕和影片的拍摄技巧、艺术成就等并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却依然与观看者对时局的关注,对民族危机的焦虑巧妙而隐晦地联系在一起。
此外,早期的电影特技也引起了中国观看者的注意。赫兹头两次放映的电影中,《申报》评论认为“以西女之舞为最。飞燕轻盈,柘枝婉转,尤妙在雾毅,随风分呈五色。忽而为绛,忽而为紫,忽为嫩黄,忽为淡碧,蹁跹妙曼,栩栩如生。”这应该是一部手工上色的彩色影片,夹杂在十余部黑白电影中格外醒目;而变幻的色彩与舞者美丽的身姿结合起来,更让人过目难忘。但是,对这部影片啧啧称美,却不能仅仅视为缺乏见识的大惊小怪或色情趣味的流露,与“咏物”传统联系起来才能更充分地理解。从《诗经》开始,中国文人就以“香草美人”为抒发怀抱的歌咏对象。台湾学者王鸿泰认为,明代后期以降的文人文化,更是以不求仕进的闲隐态度,陶醉于物的玩赏和经营之中。“士人的文雅生活其实是充满感官性的:他们将物纳入个人的感官世界中,以感官来接触、渗透物体,也因此藉由物质的感官接触来承载个人的情感,再经由情感的投注,融合物我,而形成一种脱俗文雅的生活情境。”近代之后,大量仕途不畅或无意科举的文人来到上海,原本意在“脱俗”的高度感官化的生活态度,也被近代上海日益膨胀的消费社会所悦纳。通过他们的文字,西来的物质文化产品不再难以理解,却具备了强烈的感官诱惑,挑逗起消费欲望。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无论是取景和观看的方式,还是画面中的人物和情节,对于观看者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然而,通过《申报》文人巨细靡遗的描画,无论是现场的观看者,还是通过报纸了解电影的读者,都能够以一种相对熟悉可控的方式,接受这样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
可见,中国观众到兰心看戏,并非贪图便宜的票价,更多的应是追逐一种全新的时尚。开埠几十年之后,西方人早就由可怖可憎的蛮夷,转变为追慕仿效的对象。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生活方式,都被视为文明开化的标志。而通过电影这样一种先进的媒介加以观察和研究,同样是值得嘉许的洋派做法。这样的心态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观众并不能理解电影的内容,却对其赞许有加;以及此后的几年中上海的电影放映为何不曾中断,并通过逐步改进的放映方式,成为上海市民习以为常的文化消费内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