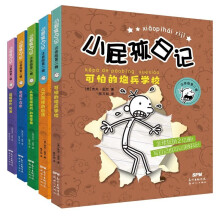大明万历二十一年的春天,对大明京城百姓来说只是平平常常的一个新年罢了。据说当今天子一如既往地懒得上朝,听说朝廷大军在朝鲜打得很胶着,太监们在江南催逼矿税也出了点儿乱子……然而这一切都不影响这座庞大城市的正常运作。
河边垂钓的老翁,市集里吆喝的小贩,街巷中打闹的孩童,城门口总是没睡醒的兵卒……一切都一如既往,北京城的城墙依然高大巍峨,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代表着统御天下的最高象征,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会望而生畏,甚至让人觉得这副景象会千百年不变地延续下去。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怀疑过这件事。
居住在城东思城坊的易平安无忧无虑地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从床上坐起来。虽然再过几个月才满十四岁,但他长得和成年人差不多高,只是看上去有些单薄,加上一张秀气的娃娃脸,总惹得四邻八舍的姑嫂大妈们叹气,然后不忍地拉他到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
事实上,易平安自记事以来就是这么长大的。
他爹是个锦衣卫百户,按理说在京城地面上也该横着走,可不知道老爹整天忙些什么,十年里回家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半年。就连易平安的娘亲在他两岁那年得了风寒最后去世,易平安的老爹也没有回来。于是小小的易平安就寄居在一户远房亲戚家,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平日里也经常会挨几个白眼。也因为没人管教,他成天混迹市井,渐渐养成了一副混吃等死的脾性……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易平安望向窗外,发现天色大亮,突然怪叫一声,连鞋也顾不得穿就往外跑,但他刚跑出房门就呆住了,一脸尴尬地弯腰:“王叔好……”
一个身着普通百姓服装的中年人坐在院子里,抬起头来看了看他,皮笑肉不笑地问:“平安,昨晚几时睡的?”
易平安挠挠头,傻笑道:“不记得了……”
中年人哼了一声:“昨夜东巷陈老四家的老狗,被人在院子外面用两颗石子直接打断了腿。平安,这事儿和你有没有关系?”
易平安苦着脸说:“王叔,那条老狗平时就很凶,我们好几个朋友都被它咬过,我也是给这畜生一个教训……要真的想使坏,我一颗石子就能打烂那颗狗头!”
“还真是长本事了啊!”王叔手指一弹,两枚铜钱飞到易平安手里,“来,让我看看你这金钱镖练得如何了!”
这位王叔姓王名峰,年纪有三十四五岁,和易平安的老爹易水寒本是同僚,善使飞镖,号称十丈之内百发百中。但五年前在一次与倭寇的战斗中身受重伤,虽被易水寒救了回来,可惜伤到手筋,这镖法再也施展不出,于是只能在京城里过上了闲暇日子,身子也开始慢慢发福。
本来投身军伍,有个伤残病痛而退出一线,这只是寻常事,易平安却因此倒了大霉。
自从得知易家的情形后,王峰就说什么“易老弟为国顾不上家,我既然闲下来了,总不能看着平安侄儿不管”,三天两头往这边跑,塞点儿酒肉钱粮给易平安寄居的亲戚家,然后就开始折腾易平安——教他读书认字也就罢了,还把当时不到九岁的易平安拖起来练那金钱镖法:“这个东西一点儿也不难,我这人算笨的,跟我师父学了六年才出师。你爹厉害,两年就练得跟我差不多,你小子鬼精鬼精的肯定不比你爹差,我给你
打个折,四年把它学会了,有个一技之长,将来袭你爹职位也硬气一些!”
可如今五年过去了,易平安想起自己学艺的经历也是一把辛酸泪:“骗子,都是骗子……手上满是茧子也没学成……”
易平安虽然心里如此想着,却不敢在王叔面前表现出来。他手腕一振,一枚铜钱便嵌在对面的柳树上,这院子里六棵柳树五年里被易平安练镖钉死了一半。
王峰把那枚铜钱从树干上取出:“入木五厘——平安,你这过年后又偷懒了吧?”
易平安嬉皮笑脸:“王叔,谁家过年也要缓缓吧……”
王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言之有理——不过现在都三月了,你还过的哪门子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