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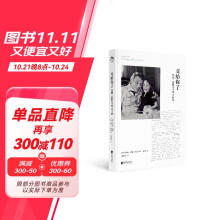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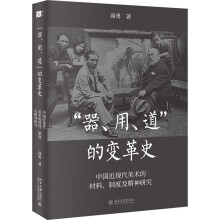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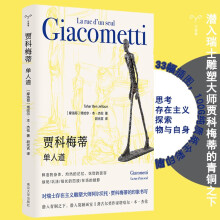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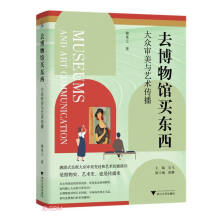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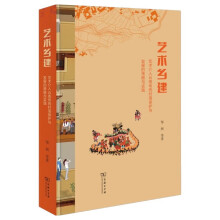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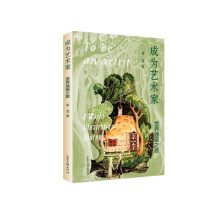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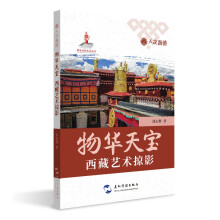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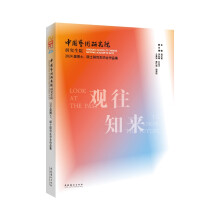
这是一次对艺术界的深度探寻,作者周婉京为多家中外知名媒体撰写艺术专栏,文章深入而有趣,另附百余帧海内外珍稀艺术品图片以飨读者。
《清思集》访谈对象涵盖:陈丹青、侯瀚如、常沙娜、张颂仁、李禹焕、荒木经惟、希克、冯博一、小汉斯、李立伟、仇国仕、翟健民、林璎、冯梦波等文艺界名宿近四十人
春妮(主持人)、翟健民(古董经纪人)、冯博一(批评家)联合作序
这是一本关于艺术品收藏的百科全书。艺术记者、作家周婉京的首部艺术访谈书籍《清思集》近日首发。作者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走访了大中华地区重要的艺术家、收藏家、策展人、博物馆从业者等过百位。《清思集》精选收入其中与40人的对谈和一些评论文章,这些人包括:冯博一、陈丹青、李立伟、希克、侯瀚如、小汉斯、何安达、黑国强、叶承耀、邓德雍、翟健民、李秀恒、仇国仕、梁义、常沙娜、黄孝逵、李禹焕、荒木经惟、张颂仁、苏法烈、杨腾集、刘家明、林璎、梁铨、刘建华、冯梦波等。和同类型的书籍相比,该书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这是从艺术记者专业访谈角度出发,专访著名艺术界人士,深层次剖析艺术圈现象,及反映艺术市场发展的图书;二、这是从古董艺术一路贯通、涵括至近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书籍。三、本书将探讨艺术市场的投资、购买、运作等问题,相信除了给予读者艺术品欣赏的知识,还会为他们的艺术投资指明方向。
《清思集》是周婉京继《一个人的欧洲》之后针对艺术鉴赏的全新力作,书中收录了百余帧海内外珍稀艺术品图片。作者结合艺术文本由一个当代的视角提出问题,通过对谈与分析逐层抽丝剥茧,着力展现现今中西方艺术界原真的生态,反映萦绕在当代人身上矛盾的困扰。这困扰中除了关于美的疑惑,还关乎着观者、读者、作者在欣赏中自处中的种种反思。
辑一 为何纪念
陈丹青:“纪念”才刚开始
木心 ( 1927—2011 ) 少小离家,中岁去国,暮年回乡,乌镇是他的故里与归处。继东栅财神湾168号“晚晴小筑”( 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 ) 于二〇一四年开放,木心美术馆历时四年建造,去岁年末终正式开馆,现坐落在西栅元宝湖畔。美术馆由木心的学生、画家陈丹青出任馆长,其建筑由贝聿铭的弟子主持建造。木心先生遗留的画作六百余件,文稿不计其数,美术馆中仅展示出所藏总量的数十分之一。陈丹青在此笔谈中详述了木心其人其事其心。木心的晚年多以转印法作画,小画之中透出一种水乡小镇独有的灵性,直教人生出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
周婉京( 下文简称“周” ):木心先生不像贝聿铭,不像陈逸飞,他似乎从未刻意融入某个华人艺术家圈子,也没有建立或巩固起自己的艺术权力。相反,他对世界文学有很深刻、内敛、自省式的了解,但他同时对所谓包容的美国社会却也保持着一种无奈又清醒的距离。你是如何看待木心旅美时的处境?与他的交往在你旅居纽约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陈丹青( 下文简称“陈” ):是的,木心很清醒,但未必“无奈”,“无奈”的意思是,他试图“有奈”,但他不曾。五六十年代,他要是想在内地发表文学或绘画,完全可以,前提是:改变自己,适应外界,就像当时许多文人艺术家那样。不。他不要这个前提。
怎样看待他旅美的处境,也有前提。绝大部分人的前提是:出国须得“成功”“融入”,小焉者如陈逸飞,高明者如贝聿铭,还有许多其他行当的成功人士,这才算得光荣,值得尊敬。我不确定你是否也持同样的价值观。你问我,我便直接地说:我不要这个前提。我在纽约就谈不上成功、融入,我与木心气味相投,恐怕基于此。
木心庄敬自强。他的前半生被压抑、被剥夺,五十六岁后在纽约重续绘画和写作,出书十余册,画作逾数百。八九十年代他在台湾广有读者,他的画也能出售,虽未致富,谈不上受穷。初到纽约的几年固然清贫,后半期,约十五年左右,自食其力,过着不失体面的生活——无数欧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是这样,此外还应该怎样呢?
非要说成功,木心的暮年收获成功:耶鲁大学美术馆为他举办特展,并巡回芝加哥、夏威夷、纽约亚洲协会等现代美术馆。这是极少数华人艺术家能得到的高规格展览。但我不在意他的“成功”。没有这些,我仍然爱敬他,只因他是木心。
周:你个人是如何着手做木心先生的研究,最早是如何开始的?面对先生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类型的创作,《 文学回忆录 》是否可视作读者接触木心、解读木心的方法论( 如若不是,你建议以何种方式着手研究 )?但这种尝试理解的方法,是否恰恰印证着我们和木心之间的鸿沟?
陈:我从未做过木心研究。他死了,他的读者( 多数是年轻人 )要我发表当年上他的文学讲习的笔记,我就发表了《 文学回忆录 》,这不算是研究。此外,我每年为理想国出版社的《 木心纪念专号 》写一篇回忆木心的文字,也不算研究。我不是学者,只是在回想一位老朋友。
《 文学回忆录 》扩大了听课的人数。但要了解木心,还得读他的著作。他的文章不好懂,譬如,他常用生僻的字词,别说年轻人,今日六七十岁一代,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后接受教育的人群也未必识得那些字词。《 文学回忆录 》是通俗易懂的讲课笔录,据说许多人开始接受他,就因为这本书,他的诗作、散文、小说,读者渐多,还是很有限。
是的,“我们”和木心是有一道鸿沟。有鸿沟,事情才有意思。我就因为看到这条有趣的鸿沟,才与他长年厮混。
周:木心先生的作品很多,每个阶段的创作和言论均能看得出他是有“大才”之人,可是似乎没有找到一个出口( 例如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年从未正式发表过作品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一辈子创作而一辈子没“出口”的艺术家,很不少。最著名是梵高,他生前从未办过展览。还有卡夫卡。至于中国内地,有大才而没“出口”的人,也不少,有过“出口”,却被批判、遗忘、淹没者,更是多有成例,如沈从文、张爱玲等。我怎么看待呢,我喜欢这类没“出口”的人,假如他果然有才华,有作品。
周:然而,读木心先生的文章,读者丝毫不会被夸张或过度渲染的“局外人”身份引起一声叹息,相反是十分诚恳的个人窥探与剖析,你是如何评价先生作品中对其文化身份的阐述?
陈:“读者丝毫不会被夸张或过度渲染的‘局外人’身份引起一声叹息。”恕我眼拙,不能懂得你这长句子。木心的写作倒是“十分诚恳的个人窥探与剖析”,所以我一点也不关心他的“文化身份”。他也从不关心“文化身份”—— 他是木心,是我熟悉的那个人。
周:木心先生的读者中,有不少“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很有热情,但同时也会有一个问题——青年人于当下社会中养成的消费习惯会不会使他们将一本书和一个复杂的人当作消费的对象。你是怎么看在商品化社会中木心被“消费”的问题?
陈:“消费”是二战后的新词语。如果人们读一本书,看一场电影,都算消费,那么古时候欧洲人读《 圣经 》,中国人读《 论语 》,比起今日年轻人读闲书的“热情”,何止百倍,你要说古人是在“消费”,也可以。现在你怕木心这样的雅人被消费了,那就被消费吧。这是个词语的问题,我没意见。
周:在此语境下,我们是否应该提倡以“反纪念式”的形式来停止纪念、缅怀,而对现状做一些切实的改变?如此一来,应如何看待美术馆的历史性与纪念性?
陈:我明白什么叫做“反纪念式”。这也是个词语的问题。但你说的“我们”,是指你,还是指我?或指别的什么人群?
我不会“停止”做木心的事,他生前无闻,留下一大堆作品和事情要去做,对他的“纪念”才刚开始。
目前,中国盖了许多美术馆,那是各地商人、官员,包括文化人做的,各有各的理由。木心美术馆是乌镇家乡子弟出钱出力盖起来的,我和木心根本没想过,也没能力做这等事。可是单单乌镇,就有两个茅盾纪念馆,一是故居,一是有他石造雕像的大纪念馆,您看过吗?
周:“我们”一词确有不清楚之处,实际想问的是,除了“纪念”之外,有何重要之事可做?而作为美术馆参观者的我们( 受众 ),除了阅读、参观博物馆以外,是否有参与到“纪念”中来的其他方式?
陈:位于乌镇东栅的“木心故居纪念馆”,目的是为“纪念”。美术馆的功能远多于纪念。除了木心作品的固定陈列,譬如尼采特展、今年的莎士比亚特展等等每年一度的项目,还将审慎、持续地接纳不同的展览,包括活动,如音乐会、颁奖会、学术讲座,等等。我不知道这样做算不算“反纪念”。如果您有更多更有效的建议,欢迎告诉美术馆。
周:茅盾纪念馆,我这次特意去拜访,正如您所言,位于乌镇北栅分水墩的立志书院坐落在茅盾故居东侧。木心先生也曾写《 塔下读书处 》( 初次发表名为:《 忆茅盾书屋 》 ),其中先生和茅盾先生相处之时的回忆描写也是亦真亦假,很动人,如果让您谈谈木心先生、茅盾先生所代表的“乌镇读书人”,不知您会作何感想?
陈:我的感想是:为什么茅盾、木心,都出在乌镇?还有,如今中国的乡镇,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文学人物和艺术家。有才能有抱负的人走了,像当年的茅盾和木心那样,但他们真的出生于乌镇,濡染江南的文脉。漫长的古代,中国的文脉大致从下往上流,如今这种流向中止了,消失了,你得在大城市才能找到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陈向宏做这些事,就是要让文脉回流,至少,一个本乡青年不必非得去大都市,就能在乌镇看到一流的国际性戏剧、像样的美术馆、图书馆。您同意吗:一个小镇,有这些,没这些,大不一样。
周:确实不一样。再看乌镇水乡的灵气,如何结合在木心的人生和创作中?
陈:不知道,这得问他。南人北人,无论做什么,都会有差别,你只要看看北欧人南欧人的画,即可了然。在中国,北人,或者中南人西南人画画,风神也多差异。
周:木心美术馆建立的初衷是怎样的,是由木心先生的话——“风啊,水啊,一顶桥”延伸而来?木心先生本人对美术馆的蓝图与发展有怎样的看法?
陈:前面已经说了,盖美术馆是乌镇家乡的计划,木心在临终的虚弱谵妄时,看了设计图,说了这么几句。他当时几乎失去意识,不清楚这就是美术馆。他清醒时,对设计师只有一个要求:将他的小画通过影像放大。此外没有任何要求。
周:木心画作以小幅居多吗?偏爱作小幅吗?展馆里引木心文字说“因为一生碰壁,不作大壁画”( 大意 ),请谈谈木心作小幅画的原因。
陈:木心画作分三类:彩墨画( 现存约三十余幅。篇幅并不小,有三幅竖构图,每幅三米多高 )、抽象石版画( 约两百多幅,篇幅不大不小 )、转印画( 这才是小篇幅,很小,数量近三百幅 )。他最早创作转印画是在“文革”末期,尚被监管,躲在家里弄,篇幅大,不便隐藏。晚年他又回到转印画,还是很小,因为已成一种尺幅上的美学,放大尺寸,就失去了咫尺天涯的效果。前两种大致画于纽约,没有尺寸的限制和顾虑,所以比较大。
周:小幅画作在录像和宣传海报,以至画集里常常放大很多倍欣赏,有没有破坏了原味呢?
陈:不但画集放大,在美术馆放映厅还制作了九米长的放映墙,放大数十倍 —— 所有美术史的作品都在画册中放大( 或缩小 ),也被放映或广告放大数十倍。原作呈现“原味”,画册印制和放映,是传播的需要,呈现另一种效果。在乎“原味”的观众,应去美术馆看原作。
周:小幅画似乎特别富有思想哲理,这个看法对不对?
陈:我个人的领会,这些画并没有哲思,而是神秘的意象和游戏感,木心先生不主张在绘画中表达所谓哲思。问题是,他本人富有哲思,一个有哲思的人画画,和一位通常的画家画画,是不一样的。但您若是在小幅画中看到哲思,也很有趣,那是您的目光和领会。
周:乌镇近年有意无意地往文化地标的方向转变,先后有了乌镇国际戏剧节,以及刚刚揭幕的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官方说辞是希望形成文化力量,反作用于旅游业。将美术馆建在“今非昔比”的乌镇,您是如何看待美术馆的处境?
陈:乌镇领导说的话,很朴实:为什么你们城里人才能看戏?为什么你们城里人才有美术馆?是啊,您将怎样回答这样的追问?
辑一 为何纪念
陈丹青:“纪念”才刚开始 / 2
何安达:吉金旧藏 见微知著 / 17
黑国强:香江藏木 古朴幽香 / 25
仇国仕:持鸡缸杯 捧长颈瓶 / 32
侯瀚如:陈箴与上海的聚散离合 / 40
常沙娜访谈之上:两代人的敦煌情 / 48
常沙娜访谈之下:石窟作画 恰同学少年 / 55
黄孝逵:再忆黄胄 废笔不废 / 62
辑二 空间与人
李立伟:失去公信力 博物馆将一无所有 / 70
台北故宫:谿山行旅 北宋巨碑 / 86
叶承耀:攻玉山房 世外明园 / 92
荷李活道有两个“老古董” / 99
希克:四十年著一本当代艺术“百科全书” / 107
“抽象”和“挪用”交错而成的中国当代艺术反思 / 119
冯博一:就地取材,造一个乌托邦出来 / 128
辑三 进行时
苏法烈:当“天真一代”遭遇“外国骗子”?/ 144
张颂仁:从艺术推手到水墨学者 / 151
常玉:静物无言 玫瑰有情 / 159
李禹焕:用“非也”阐述身份 / 165
荒木经惟:“吻”过香港的男人 / 173
杨腾集:“跳出来的”才是好作品 / 179
刘家明:与艺术家共同成长 / 186
小汉斯:科技带来新的“展示特性”/ 192
辑四 闻弦歌知雅意
翟健民:公道杯不能失公道 / 204
邓德雍:冰肌玉骨 不鬻于市 / 211
密韵楼:一页宋纸 一两黄金 / 219
梅景书屋:收藏绘画 兼修并重 / 228
李秀恒:明清官窑 锦瑟华年 / 235
吉庆堂:轻轻捋一遍“灯草口”/ 242
白石书画:闲步归来 旧日老屋 / 249
承砚堂:岭南风月 古砚养墨 / 255
梁义:君子字画 雅集之趣 / 261
辑五 变奏曲
致艺博会时代的信:“强心针”不能救命 / 270
“触”是组序的基础
——由洪浩个展“反光”引发的思考 / 277
林璎与她的诗意针灸 / 282
域外的“空”:分析梁铨艺术创作中的“自我放逐”/ 288
潜意识的瞬间 致未来的自己 / 295
白纸非纸:刘建华书写可感知的温度 / 301
媒材上的跨度,记忆上的承接
——浅析冯梦波艺术作品中的“光韵”/ 306
闲话“文青”生活 / 314
后记:谈一场不空泛的“恋爱”/ 326
参考资料 / 328
温馨提示:请使用惠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我们和木心是有一道鸿沟。有鸿沟,事情才有意思。我就因为看到这条有趣的鸿沟,才与他长年厮混。
——陈丹青(画家、作家、木心美术馆馆长)
一间博物馆并不只关乎你展示什么样的艺术品,更关乎你怎样呈现艺术。
——李立伟(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创馆馆长、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首任行政总监)
实验有可能失败,有可能成功,那么无论是艺术还是其他行业,都是要不断否定、建构、再否定、再建构。
——冯博一(策展人、评论家)
贯穿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没有到位的画廊系统,没有互联网,没有书。而对我来说,收藏从来不是买卖结束、关系终结这么简单。
——乌里·希克(前瑞士驻中国大使、收藏家、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创办人)
时至今日,策展不只单纯对艺术史、文化遗产负责,它已变成一种传播手段,作为策展人所打造的展览应向公众提供未尝试过的体验,而非是插图或立体书。
——小汉斯(伦敦蛇形画廊联合总监、《策展简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