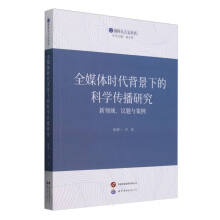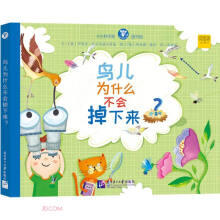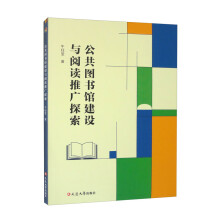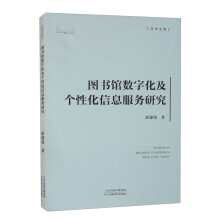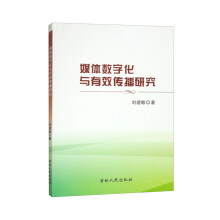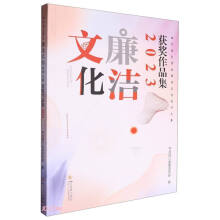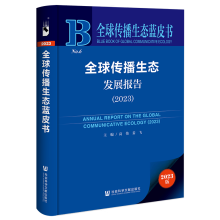《新闻是匆忙中写就的历史》:
这一切困难,归根结底还是学术思维的特点在作怪。学者的头脑和普通人的头脑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前者更加强调和看重一致性、清晰性、规范性、逻辑性。然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并不总是、甚至很少符合这些学术期待。是“一中求异”还是“异中求一”?这是待解的难题。
至于“定量”还是“定性”的优劣高下之争,实在是“伪问题”,没有必要为此而争论。一切取决于研究问题,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有些研究问题,一看就知道必须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解决;另一些问题,则要求定性研究方法;第三类问题,需要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组合。还有无数的超越这三类问题的“大”问题,无论用何种方法组合都无法研究,无法解答,像诱人的大仙桃,让最聪明的孙猴子也无处下嘴。
于是,我们的学者就处于两难的境地:若研究可能产生根本性的理论突破的问题,方法无法支持。如果运用了学界不认可的方法,即便产生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也难以得到承认。那么,除了传播学的欧美各大学派的方法——理性范围内的思辨和实证,是否还有“第三条路”?
4.传播学理论创新的评价标准及思维障碍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评价标准”这一问题。下文将分析这些既有标准如何成为对理论创新可能的潜在阻碍。梳理统计20多年来东西方各种学术讨论场合记录的学者学子评论他人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标准,与新闻理想竟然高度重合:客观、公正、全面、平衡,还有“严谨”。常听学生、学者说:要多引用权威的观点。学生普遍认为这是“客观”的表现。我不禁要问:所谓客观又是谁的主观呢?除非研究者完全采取“旁观”的心态,否则,这种“客观”不啻掩耳盗铃。公正?对材料、数据、事实的公正的分析?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将材料“托付”给电脑处理而获得这一幻觉。但在“托付”之前的步骤和结果产生之后的解释,是否依然由学者完成。至于“全面”,即便是一个简单的个案分析,依然面临着“人不是全知的”这一致命挑战。当然,这不必令我们太沮丧,因为庄子笔下寓言中那些“高人”的智慧使我们相信:有的人知识很多,但没有见解;有的人常识缺乏,但见解深刻。自然,我们的教育致力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有独到见解的人。但古代哲人留下的寓言启示我们:人在认知过程中,的确有可能不尽知其然而却尽明其所以然,亦即掌握规律。至于中规中矩“讲两面理”的“平衡”,本身无可非议,但人类知识的演变史昭示我们:思想、理论、学术,总是以极端的方式得以突破。
经常阅读本学科国际顶尖期刊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研究论文总附有超长的参考文献目录,甚至了解此一行情的国内学者常常以此作为标准鞭策学子:你的观点很好,材料也充分,但是你的参考书目太少了。这让人想起一组比喻:做学问,究竟是像蚂蚁那样“知识搬家”,还是像蜘蛛那样“搜肠刮肚”,还是像蜜蜂那样“采来百花酿新蜜”?第三种路径显然容易引起有学术理想的人的共鸣,但也会被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指斥为“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
这些都是低层次的纷争。当现实世界没有出路,我们应该回到学术的终极目的上来,寻求超越。学术有为社会的学术,为人生的学术,也有为人心的学术。少有学者提及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我认为应该是揭示真理,洁净己心,进而洁净人心。具体运用到传播学,就是致力于洁净信源、信道、信息、传播者、接收者。那么,用什么方法实现这一目标呢?显然,上文所述各种方法无能为力。
然而,我们并非企图挑战、否定或颠覆现有方法,因为这种企图也是违背科学思维规律的。我们所做的乃是补充现有的方法,至少是提出现有方法难以支持和验证的问题和观点,以期促进突破和创新。
一旦触及终极问题,我们就要逆流而上,追溯西方文明及其思维方式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前者注重理性,知而信;后者相信启示.信而知。一个多用脑,一个多用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成果无须说,其“后果”之一就是将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多数人的思维侧重点转移到“人”,从心灵转换到头脑,几百年来我们就一直在自以为解放的虚幻满足中,在理性的边界里打滚,而实际上是进入人类自设的牢笼。人类最长的长征不是奔赴南极北极第三极,也不是飞向太空或成为海底蛟龙,而是走出自我的樊笼。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确定,传播理论创新的希望在于揭示“直抵心灵的传播”的奥秘,让学者的理论首先赢得自己的心,然后再启发(而非指导)更多的人赢得人心。最后,最难的问题就是关于传播和人心的真理如何获得?难道它一定是理性思考及其指导下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学者一般不愿意承认自己学科范围内的问题居然有“无解”的,正如政治家也总是许诺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找到解决方案。中国学者如果不破除对于西方舶来的传播学的“起源迷信”和“方法迷信”,恐怕还要在这个心灵迷宫里兜更大的圈子。“学术自信”并非盲目的厚此薄彼,而是祛除心理劣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