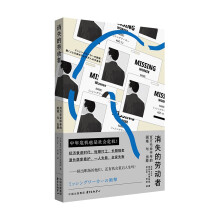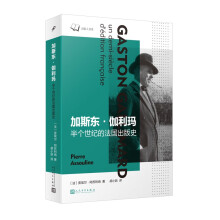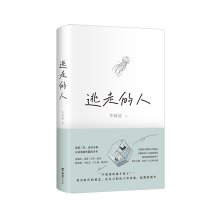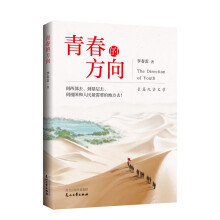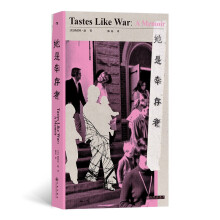胡可:耄耋老人心系“学生军”
胡健
2010年春节前,我去看望著名剧作家、耄耋老人胡可老先生,恰遇威海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人来采访、拍摄。他们的话题非常有趣:寻找当年的学生军。这说的是“七七事变”以后活跃在北平西北郊的一支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由于有大批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而被老百姓称为“学生军”。胡老说,这支游击队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抗日军”,不大被人记得;但因为佩戴红蓝两色袖箍,还被老百姓们称为“红蓝箍”。
“红蓝箍”?我表示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
胡老说:“是啊,是啊,如果再不好好宣传宣传,这段历史就真的会被北京人忘记了。”
此事的契机,是威海的一位年轻人常征,为了记述当年外祖父在“学生军”时的事迹,来北京寻访当年的见证人。威海电视台抓住这个线索,跟踪拍摄,又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兴趣。这位年轻人的外祖父正是当年游击队的参谋长常戟武同志。
胡老也曾是这个“学生军”里的一员,是个小兵。在电视镜头前,胡老展开了他的思绪。
年龄最小的小兵
1937年的夏天,16岁的胡可从济南到北平投考高中,他曾经在北平的灯市口上过小学。这次来,经过天津的时候,火车停了很长时间,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车到丰台,只见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枪进到车厢里来盘查,气氛十分紧张。到北平后他才知道,原来盘踞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同驻守在宛平城卢沟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说起的那个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北平城里人心惶惶,少年胡可所住的公寓在西单一带,在这里能清晰地听到城外传来的炮声。不久炮声沉寂下去,日本军队开进了北平,只见插了太阳旗的军车在长安街上疾驶,府右街口的日本哨兵大声地呵斥着路上的行人。他立刻感觉到自己已经同东北同胞一样变成了亡国奴,心情十分痛苦郁闷,投考学校也没有了心思。
他的哥哥胡旭在北平上高中,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一天晚上胡旭悄悄来告别,说他已经参加了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今后不可能来照顾小弟弟了,嘱咐胡可自己安排今后的生活。
胡可听说了抗日游击队,无异于在黑暗里见到了火光,他执意要哥哥带自己同去。胡旭先是说他年纪小,游击队可不是儿戏,后来看拗不过弟弟,也就同意了。第二天他们通过了西直门日本兵的哨卡,搭公共汽车到了西北郊。那时北平的郊区还是荒僻的农村,公共汽车也只通到燕京大学(今天的北京大学)一带。他们下了车就顺着田间小路走进了秋虫叫闹着的青纱帐。刚下过雨,庄稼地里散发着泥土的潮气和禾黍的清香。走出几里地,他们在路旁见到了坐在瓜棚里放哨的一个留着两撇胡子的胖老头,胡旭管他叫唐三爷。在唐三爷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一个叫作大苇塘的小村庄,在一所院落里找到了这支游击队第三总队的队部。 这里聚集了不少人,有的持枪,有的徒手,有的是学生模样,有的是老百姓打扮。还有一些人穿着和尚一般灰色的短衣,个个面色苍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刚从监狱里被解救出来的犯人。引人注意的是,人们的左臂上都佩戴着红蓝两色的袖箍,屋里的几个女同学正在一面为大家缝制着这种袖箍,一面吟唱着人们十分熟悉的救亡歌曲。听到这些歌曲,看到这些袖箍,胡可顿时觉得来到了亲人中间,许多天来那种当了亡国奴的郁闷感觉一扫而光。胡旭把他介绍给一个挎着驳壳枪、满脸胡楂儿的高个子中年人之后,就回他的第一总队去了,这个中年人就是这支游击队第三总队的队长刘凤梧。
这支游击队是由“七七事变”以前潜入关内的少数东北义勇军和北平城里出来的一批进步学生作为骨干组成的。学生大部分是“民先”队员,其中有些还是中共党员。党员们遵照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指示,通过团结下层官兵和对游击队领导人施加影响来实现党的要求。当时,北平德胜门外有个河北省第二监狱,里面关押着七八百名犯人,包括几十名政治犯。北平沦陷以后,为了不使这些被捕的同志落到日寇手里,党决定趁敌人尚未接管之际,尽快设法解救他们。游击队司令赵同也想借此缴获一些枪支,壮大自己的队伍。当时游击队的决策者除了赵同和他的几个亲信以外,还有高鹏、纪亭榭、汪之力等同志,汪之力实际上是我党派到这支游击队里来的代表。他们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在一天夜里,由会日语的义勇军同志冒充日本兵,骗开了监狱门,缴了狱警们的械,解放了所有的犯人。
砸开第二监狱这件事,震动了沦陷后沉寂的北平城,由于其过程具有传奇色彩,便长期被人们口头流传。这些犯人大部分参加了这支游击队,其中的政治犯有许多是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他们很快成了游击队的骨干力量。那些普通犯人虽情况各有不同,也都在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凝聚在一起。当天夜里,少年胡可和这些犯人睡在一条炕上,他问躺在身边的一个犯人因为什么坐了监狱,那人坦然地回答说,因为杀了人。他当时刚16岁,虽读过《水浒》《三国演义》等有着杀人情节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