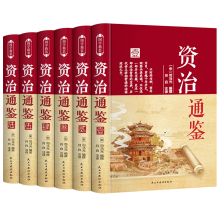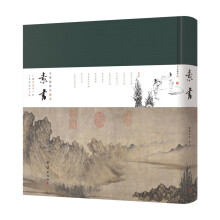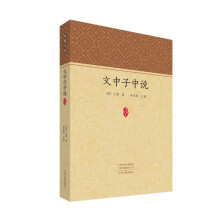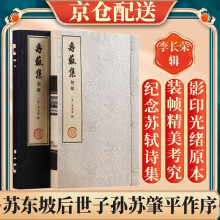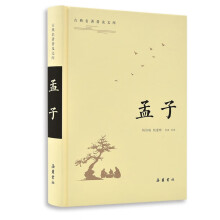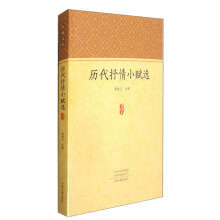《国学要义精讲读1》:
经典需要细读和精解。上述两则的生动记述首先告诉我们,原始儒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人”,其实就是“君子”。宋代周敦颐曾提出“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修养论,后人简称之为“三希真修”。其中所谓“天”乃是“天理”所存处,在具体指向现世人格修养的领域里,“希圣”显然属于最高境界的人格修养诉求。但是,孔夫子却告诉大家:
其一,如果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作是“仁”的理想境界,那尧舜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也就是说,尧舜仍然处在“仁之方”的发展道路上。求其言外之意,是在说“圣”作为君子人格理想的完美实现,作为儒家仁政理想的完美实现,永远存活在人类的理想之中。若要以这种完美理想为标准来衡量现实中的人格典型,即使杰出如尧舜,也是有缺陷的。而尤其重要的是,被孔子确认为“必也圣乎”,从而已经高于传说中“三代盛世”标志人物尧舜之治国成就的社会文明内涵,其实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民众福祉之追求。很清楚,君子人格理想的社会政治内涵,具有民生主义的思想性质。
熟悉中国儒家文化之发生原理与发展轨迹的人,至此自然会联想到,关于君子人格的讲求之路,主要是沿着“内圣外王”的方向来推进的。从“内圣外王”的内在价值规定出发.孔子对尧舜的批评就更显得意味深长。如果说中华道德政治的基本理念,是“道德规范权力”和“德政以民为本”两大原则的实践统一。那么,孔子把检验圣人君子的客观标准,确定为“博施济众”的民生政治实践,这就意味着古典民本主义的实质是民生主义。不以民生主义为内涵的民本主义,很可能成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种政权获取机制中的权宜之计。更何况,孔子与子贡借“问仁”而阐明的圣人君子之道,最终是一条永远在路上的民生政治道路。
其二,同样是批评尧舜,“博施济众”的出发点和“修己以安百姓”的出发点,显然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前者体现了物质上的民生主义,那后者就体现出精神上的民生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关键在于“修己以敬”的那个“敬”字!
朱熹曾说:“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有现代学者指出,“畏”是“敬”的极度形态,儒学伦理因此而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深沉宗教意味。
通俗地讲,君子自我修养之际,仿佛与孔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说的“天命”“圣人”同在,于是就会心存敬畏而庄敬自重,就会心怀虔诚而自尊自信。待到“修己以安人”,也就是进入人们常说的“推己及人”的君子人格之人际关系,除了彼此共同的敬畏之心的自然沟通之外,必然还有彼此之间“美人之美”“自尊尊人”的精神内容。循此以进,然后抵达“修己以安百姓”之际的“主敬”境界,“修己以安人”的一般人际关系,值此转化为“修己以安百姓”的社会政治关系,和“修己安人”比起来,“修己以安百姓”讲的是社会上下关系,是帝王君主与百姓大众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领会,“尧舜其犹病诸”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正在于没有真正实现上下之间的相互敬重,换言之,孔子值此而提出了敬畏百姓和百姓尊严的问题。综上所述,孔门师生“问仁”与“问君子”之际的人格理想阐释,不仅指明了永远的民生政治主题,而且阐明了鲜明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