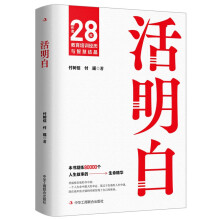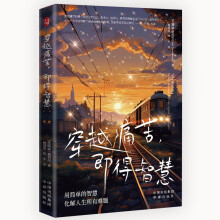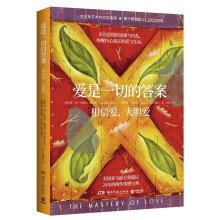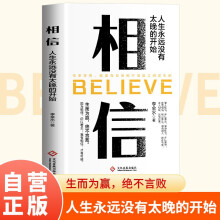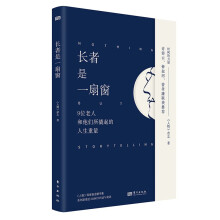《孤独的灵魂》:
没死。我想到过死,那是一种绝望,或者说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活着或死亡,没有什么区别和意义。晚睡晚起,看书,吃饭,街上游荡,上网,写作,半夜入眠。电话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不是电视购物上超长待机之类的夸张说辞,而是我很少打电话。
死亡。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我一度地思考这个问题,有生就有死,大多数人选择自然死去,他们是坚强的,他们能够承受住生命给予的磨炼和痛苦,能够承受得起生命里的不幸和上天赋予的苦难。一部分人选择自杀,自杀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心理受到某种不能承受的打击或灾难;还有一种是思想到达某种境界,无法超越自己,而内心极其渴望超越自己,无比地痛苦,无比地忧郁,就像作家海明威。
我是一个害怕疼痛的人,从小到大没打过针,每次感冒都是吃药,高烧不退就吃退烧片,每次吃半片,大人才吃一片,到我家的赤脚医生,后背背着一个药匣子,里面装了各种神奇的药和一些针头针管,我因看了隔壁家阿姨生病了,赤脚医生在药匣子里取了一个针头,装在针管上,然后吸取一些药水,拔下阿姨的裤子,棉签一抹,针头就扎进屁股。阿姨的嘴巴就开始抽搐,眼睛紧闭,做出痛苦的表情,所以每当我看见这个药匣子的时候就号声大哭,父母也就不让医生给我打针了。我知道电影里面有一种舒服的死亡——吃安眠药。
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一种比吃安眠药更好的方式——写作。写作是一种慢性自杀,慢慢掏空你的内心,触摸你的思想,撞击你的灵魂,压抑,空虚,无聊慢慢地补充进去,压抑着人神经错乱,压抑着人不停地写作,越写越空,无声无息地孤独地死去。
没有脚气。小时候我养成的习惯非常好,晚上洗脚,早上刷牙,我的牙齿是我们班上最白的,老师经常要我站在教室的讲台上,张大嘴巴,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让每个学生来参观,我就像一个北京猿猴人被同学无数次的免费参观。其实,我想给老师说的是我的脚也很白,而且没有脚气,有一次参观完我的牙齿,我鼓起勇气悄悄地对老师说:“我的脚也很白。”老师说:“你的屁股白吗?是不是想脱掉裤子也让大家参观参观?”没有身材。九十八斤,每次都是这个数字,没有超过一百斤,瘦得可怜,比很多女生都轻,所以上大学那会儿她们有时说,我是她们的偶像。
没有长相。两腮、下巴有胡子,所以此生就不要幻想做美男子了。脸上曾有一个痣,上中学的时候在大街上晃荡,有个酷似道人的老头,白胡子白睫毛,穿着一身黑衣,颇有几分神秘,在地上摆了一个脸谱,上面有很多痣的解法,老头子捋着胡须,给围观者解说痣的好坏,旁边的包里自然是他的法宝,里面装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药水,我记得他给我脸上的痣点了一下,收了我两元钱,说不要拿手动,丑几天就会自动掉,我半信半疑的丑了三天,果真掉了,就是有个坑,不过比先前好看了一些。但依然长得是对不起观众的那一类型,后来在电视上发现我的那个痣和李连杰脸上的痣一模一样,后悔的要死,当初为什么没有看脸谱上那个痣的解说,这或许是一个好痣,所以我时常在街上溜达,看有没有可以复原回来的药水,至今未找到。
没工作。出校门之后,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上一天休三天,与其说是份工作,还不如说是份兼职,半年后,辞职了,因为颖。
没文凭。大四的学费我不知道花哪去了,没有交学费,毕业证没有拿到,银行还有贷款。在如今社会,学历已不是你有没有大学的经历,有没有真才实学,而是有没有一张纸的上面印着××大学毕业证,不管有没有真才实学。或许你读的是北大的中文系,出来却是一个卖猪肉的,或许你读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舞蹈系,出来却是一个酒吧的陪酒女。所以每当有孩子的家长问我,他们孩子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时,我都苦笑不言。
没钱。自然没车没房。
在我的印象里西安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高考结束后,朋友们去南昌玩,我没去,因为女朋友。去的都是一对一对,单身去的回来就是情侣了,我去就是给他们当电灯泡。
想和她在一起,毕业也许就是分离,谁也不知道谁将会去哪个城市上学。
上帝很眷顾我们的爱情,录取的大学在同一座城市,虽然一个在城市的最北边,一个在城市的最南边,但是依然很感谢上帝的恩典。
大三暑假时候,我们分了,没有原因,没有言语,突然彼此不再联系,或者心里都明白,没有必要找个荒唐的理由,让大家泪流满面,那是对死亡爱情的一种祭奠。
爱情就是相互探秘,男人对女人的探秘,女人对男人的探秘,大彻后,爱亦无存,空余习惯、回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