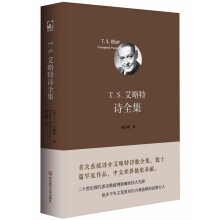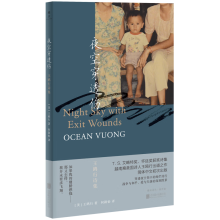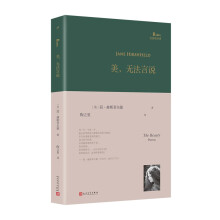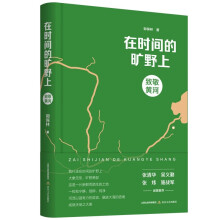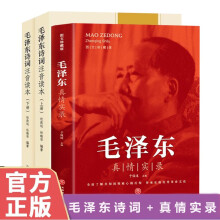我十二岁那年夏天,父亲母亲带我跟哥哥开车去内华达山中露营。在一片幽深、人迹罕至的杉树林里,我们度过了平静的夜晚。早晨,父亲母亲去晨跑,或者做点有小孩在身边时不方便做的事情,留下哥哥陪我。但我哥也觉得看守一个比他小六岁的女孩太无聊,遂离开营地到附近湖里游泳。出于哥哥的责任心,他把烤肉用的铁叉拿出来,放在我身边。
我在帐篷外煮咖啡,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忽听到脚步声。回过头去,见一个人正从林子深处向我走过来。他的长发披散在肩头,满面乱须,衣服破旧,步子不但迟缓,还踉踉跄跄的。一开始我以为他受伤了,或者在山谷里迷了路,跋涉得太久。不过我还是抓起了手边的铁叉。
他在距离我几米的地方主动停下,喘着气向我打招呼,年轻的女士,你好,请别害怕,我没有恶意。
他说话口音很怪。我握紧铁叉说,我爸妈就在附近,我一喊他们就会回来。
他说,我绝不会伤害你,我只是想借一点东西……他似乎正处于一种奇怪的痛苦之中,想要继续说话,却无力地垂下头颈,身子也随之软瘫下去,跪倒在草丛里,提起双手掩住脸,肩膀微微颤抖。
我虽然仍保持警惕,还是动了恻隐之心,问道,喂,你要什么?水?食物?我可以丢过去给你。
他不抬头地摇头,长发纷乱地抖动,像风吹过一丛野草。半晌才抬起头来,像是那一阵发作过去了。
我从餐盒里拿起一块三明治,问,要吃这个吗?放了金枪鱼和腌黄瓜,切了边,是我跟妈妈做的。
他苦涩一笑。谢谢你,我不饿。
他大概三十多岁年纪,其实还算得上年轻人,栗色头发,两枚形状漂亮的眼睛,围着长长的睫毛,若忽略风餐露宿加诸的黧黑和粗糙,那张脸是很好看的。
我问,你到底需要什么?能帮你的,我会尽量帮忙。
他瞧着我,仿佛下了很大决心,开口道,善良的小女士,我不知道我是否该向你求助。如果你有耐心听我讲个故事,讲完了,要不要帮我,由你来决定。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十年前,我在都柏林的音乐学院上学,是中提琴专业的一名学生,梦想是某天以首席中提琴的身份,坐在国家歌剧院的乐池里。我跟三个好友组建了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每次学校开交响音乐会时上台表演,有时也到外边演奏挣点小钱。大学四年级初夏,我们这支小乐队受邀到雅典去,参加一个国际青年四重奏比赛,经过初选复选决赛,得了第四名。第一名是瑞典的一个女子铜管四重奏,大伙也没什么话说——谁让她们都是盲人姑娘呢。比赛结束那天夜里,十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男生女生爬上卫城山,在帕特农神殿前的石阶上整夜拉琴唱歌,傻笑,喝酒,抽大麻。为勃拉姆斯干杯!为大熊星座干杯!为贝多芬的梅毒干杯!为乔治桑的小狗干杯[1]!直到所有人都烂醉如泥……无论什么时代的少年人凑在一起,总会是这德性。
是我们乐队的小提琴手把我摇醒的。糜乱的狂欢夜过去,时已清晨,不知什么时候人们都离开了。我就那么迷迷糊糊地被拽下山,赶到火车站,上了火车。
回到学校,我开始准备毕业考试。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哪儿不一样呢?开始时,它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心里总会慢慢涌上难以形容的痒和不满足,若隐若现,就像渴了或饿了,却又不知道能解渴解饿的是什么。
那时我有一个女友,她比我大几岁,刚进入一间公司做文员。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旧公寓。那段时间,我变得特别喜欢吻她。夜晚入睡之前和早晨醒来之后自然要缠绵个没完,每天下午,我又以前所未有的急切到公交站去等她下班,一俟她踏下车门,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去,搂住她的腰肢,用嘴堵住她的嘴唇,不歇气地吻她。
每次亲吻过后,那种“痒”便暂时平息下去。
白天练琴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地回想亲吻的情景,慢慢明白那种迫切的痒,就是——要得到吻。像吸毒的人渴望毒品一样。每次我捧着她的脸,将之拉近,浑身血管就开始瑟瑟发抖。鼻孔里轻轻喷出的气息,肉体透出来的香气和热力,嘴唇和脸颊的摩擦,都令我疯狂。而她双手紧紧箍住我的腰和背,指尖那无意识的忽轻忽重的用力,还有沉醉的神情,更让我脑中一阵阵出现狂热的空白。
起初她以为爱情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喜不自胜。但很快她发现我的热情仅限于亲吻。我不再愿意陪她说话、散步,甚至连做爱都不感兴趣。我就像初生婴儿迷恋乳房一样,无理智地迷恋和索要她的嘴唇。甚至中午我也忍不住跑到她所在的办公楼去,请求她下楼来赏赐我一个越来越不耐烦的吻。
一切变化,都发生在卫城山上那夜之后。难道亵渎了神祗,遭到神的诅咒?或是被卫城山上的怪物附体?又或从哪个人那里染上了一种新型性病?
我去找我的好友,那个小提琴手。问:在卫城山那一夜,我们都做了什么?
他说,你也在啊,你不知道?
我说,我醉得太早了。
我没比你晚太多。咱们集体向瓦格纳敬酒之后,那个保加利亚的女吉他手过来坐在我大腿上,吻我;小号手跟女长笛手搂在一块儿;也有人过去跟你亲吻……
我问,吻我的人是谁?
他摇摇头,很多。大家都醉得太厉害。你记不记得咱们玩儿“敢不敢吻”的游戏?你第一轮就抽到那对双胞胎兄弟……我甚至怀疑我也吻过你了,哈哈。
我喃喃地说,是吗?这时,我的瘾头已经发展到单是听到“吻”这个词就一阵奇痒难耐。我忽然毫无预兆地扑上去,双手捧住他的脸,把嘴唇压上他的嘴唇。
他惊得呆住了,半天才想起挣扎,一把把我推倒在地,又羞又怒地捂住嘴。这是自从我得了“神秘怪病”之后,第一次亲吻女友之外的人。我失望地发现,抢来的吻一点滋味都没有,根本没法杀瘾。
我向他解释我的“病”之后,他的怒火转变成了惊诧,糟糕,我不会被你传染吧?……
除了我和小提琴手,那一夜参与狂欢的还另有八个人,三个女生五个男生(最糟的情形,是我吻过了他们所有人)——利物浦的女长笛手,保加利亚的女吉他手,基辅的女小提琴手和男大提琴手,斯特拉斯堡的小号手,那不勒斯的圆号手,还有土耳其安卡拉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两个都是吹单簧管的。
要想逐一找到这些人,当面询问端的,就得跑遍欧亚大陆。那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
幸好我还记得他们所在的学校——每个城市的音乐学院也就那么几所。我给每个人都寄去一封信,委婉地询问:在卫城山上度过那一夜之后,可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在你身上?
斯特拉斯堡的小号手:看到你的信太惊喜了!我会永远记得我与你的吻。我一直想念吻你的感觉。要来斯特拉斯堡找我吗?随信附上我为你写的一首曲子。
利物浦的女长笛手没有回信。
保加利亚的女吉他手:为什么是你给我写信,不是你们乐队的小提琴手?!那夜我吻了他,他说他爱我,说会写信给我,说会坐火车来看我。帮我问他他还记得吗?……
基辅的女小提琴手和男大提琴手:订婚算是不寻常的事么?我爱了他三年,从第一次在学校音乐厅看到他拉琴那一刻。那夜我终于有勇气主动吻他,然后坦白心意。雅典娜保佑!我们正在筹备婚礼。祝福我们吧!你愿意带着你的乐队来参加婚礼吗?婚礼举行地址是……
寄给那不勒斯圆号手的信,是他的姐姐替他回复的:不得不悲痛地告知您,吾弟已于上月意外身故,在一次街头音乐会中,他们与该地盘的黑手党发生纠纷……
安卡拉的双胞胎兄弟没有回信。
我不知道真相是掌握在那几个没回信的人手中,还是知道真相的人不愿坦白?……我本打算先把考试对付过去,再解决这事儿,然而恰巧是在毕业考试期间,最严重的一次发作出现了。
当时我正在学校音乐厅。院长和教授们在观众席第一排正襟危坐。考试第一题是一首柏辽兹的曲子,第二题是自选协奏曲,第三题完全自由选择,也可演奏个人作品。
第二题,我选了一支斯塔米茨的D大调协奏曲。刚拉到一半,忽然感到脑袋发晕,就像发条耗尽的玩具一样动弹不得,嘴唇阵阵麻痒,执弓的手也变得软弱无力。琴弦上发出毫无旋律可言的噪音,在安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教授们集体蹙眉。副院长敲敲桌子,年轻的先生,集中精神!这是第二题,你已经直接跳到你自己作的曲子啦?重来一遍。
我躬身喃喃道歉,再次把琴弓架在琴弦上,却一节谱子都想不起来了。脑中像有一个声音在怒吼,吻!吻在哪里!我需要人来吻我!嘴唇!我要嘴唇!热乎乎的,温存的,柔软的,湿润的,嘴唇……我猛地将琴和弓往地上一掷,跳下台子,从目瞪口呆的教授老师们身边飞奔过去,夺门而出。考试是对外开放的,观众席上还有不少来旁听观摩的低年级学生和校外音乐爱好者,所有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在短短一瞥中,我猛然觉得人群中某张脸十分熟悉,那对目光……但当时我除了要找到一个吻,什么都没法想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找到我女朋友的。一见到她,我就像即将溺死的人扑向氧气瓶一样扑向她的嘴唇,完全不理会屋里其余人的诧异眼光——那间屋是她公司的会议室,她正在陪着上司与客户开会。
被拖出大楼之后,我紧紧搂住她,半强迫地吻她,然后在路边瘫坐下来。她用又怜悯又嫌恶的眼神瞧着我,说,刚才那个吻,就算是我送你的分手礼物吧。
失去女友,我对吻的狂热变得无处发泄。我与别人说话的时候难以集中精力,总是盯着别人的嘴唇。分手后第三天晚上,我到酒吧里喝了个烂醉,走出来时,有衣着暴露的女人上来搭讪,悄声问,甜心,去你那儿还是我那儿?
我说,不用去你那儿,也不用去我那儿,就在这儿行不行?
那女人诧异地环顾四周,笑道,你的喜好是让街上的人看着?
我摇头,不,我只要你在这儿给我一个吻就够了,我付同样的价钱。
那女人还没回答,我听到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女士,请到别处揽生意吧,我的朋友醉了。
回头去看。一个纤细姑娘,短发包围着一张秀丽的脸蛋。
我记起了这张脸,她是那位来自利物浦的长笛手。我大叫起来,是你!你去了音乐厅,我毕业考试那天,你就在观众席上!
她点头,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是特地来向你道歉的。
回到我的公寓,她给我解释了这件事——其实,几句也就说明白了:那夜在卫城山上,喝醉了的人们胡乱互相亲吻,她吻过我,就此把我变成了跟她一样的“吻瘾者”。
吻瘾者,就是对吻上瘾、无法自拔的人。吻令他们亢奋,幸福,飘飘欲仙。瘾头一旦发作,就一定要得到亲吻才能平息。
我问,在你吻过的人里面,有多少会患病?
她摇着头,万中无一,我吻过很多很多人,你是第一个因我而染上瘾的人。不过,我不也是被别人传染上的么?
为什么……是我?
她再次摇头,我不清楚,也许本来你就不在乎肉体和性爱、在潜意识中非常迷恋亲吻……这就像一群人中有一个人感冒了,大部分人都仍能保持健康,只有少数几个人会被传染。她又纠正道,这不是病,绝不是!这只是一种奇特的……瘾。
我苦笑道,天天脑子里晃荡的全是嘴唇,这样还不算是病态?
她冷冷道,这世上有人迷恋权力,有人迷恋金钱,有人迷恋性爱。他们会公然说“我宁可一辈子没有子嗣,也不能一天没有权力”[2]。比起他们来,迷恋嘴唇、舌头和温情带来的快意,算什么病态?也许我们才是世间最懂得快乐为何物的一群呢。
……第二天早晨她就离开了,在我额头留下一个礼节性的轻吻。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