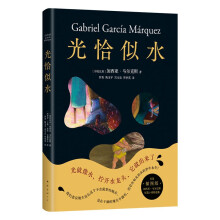她的眼睛很大很美带着某种忧伤
躺了好久,还是难以入睡。我决定出去走一走。院子里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给我一种梦一样的感觉。我意外地发现,一个房间里还亮着灯。
透过窗户缝儿,我看到了老人。他穿着一套工人的蓝布衣服,在那里对付着一台烫金字机。他的前面燃着一个火盆。过了一会儿,老者的手离开烫金字机,凑到火盆前,借助它的光,我看到一个东西。我的目光立即被他手上捧着的东西吸引,那是我所要寻找的那本古书。
老人捧着它,嘴里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这个过程中,老人鼻梁上架着的一副珐琅眼镜摇摇欲坠,颌下长长的山羊胡子微微抖动。天哪,难道他竟然认识那些奇形怪状的字?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凝神细听,只听老者缓缓读出的是:“幻不自有,必依于真……”
老人的声音缥缈,仿佛自天边传来。我的心突地一颤:美丽的梦幻真的是无根的吗?真的是从我的丑恶中生长出来的吗?就像那些月季花,必须从土壤里生长出来?我的眼前,一个白衣女人倒退着飘出窗子,飘向空中,像一朵花一样飘着,一瓣一瓣散开。
“我的名字叫薛荔。”她的眼睛很大很美,带着某种忧伤。
天际处又传来老人的声音:“如无真者,幻觉是谁?”
难道真是这样?丑恶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看到一些美丽的幻象?一个女人用发颤的声音,动情地对我说:“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就是我的男人。”我被她抱在怀里。她是很美丽的,低头的瞬间,一头长发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她静静地看着我,眼睛很大,瞳仁乌黑发
亮,如缀在夜幕上的星星。
“我的名字叫薛荔。”她的眼睛很大很美,带着某种忧伤。
“泯此觉相,幻复何有?”老人沧桑的声音又高起来。
难道,只要我的丑恶土崩瓦解,那美丽的幻象就会烟消云散?
我穿过码得整整齐齐的绸缎,红的绸缎,绿的绸缎,黄的绸缎,柔柔地滑过我的臂膀,绸缎铺里樟脑丸的味道悠悠地进入我的鼻腔。穿过瓷器的世界,一个宽阔的空间呈现在眼前。尽头,有一张白色的桌子、两把白色的椅子,一个白衣女人独自在那里,安详地坐着。她缓缓地转向我,眼睛里闪过一道光亮,柔柔地向我开口说道:“小男人,来呀!”
“我的名字叫薛荔。”她的眼睛很大很美,带着某种忧伤。
“已有此觉,幻象斯起……”还是那老人的声音,好像一条长长的带子,在我身上绕了一匝又一匝。
难道正是因为有我这丑恶的河床,美丽的幻象之水才潺潺流淌?
我慢慢地坐下,坐到她的对面。我看到了她的一双大眼睛,瞳仁乌黑油亮。不,那瞳仁并不是乌黑油亮,它正在变成蓝色。那是一种湖水的颜色,并且波光粼粼。
“我的名字叫薛荔。”她的眼睛很大很美,带着某种忧伤。
“此能觉者,是名真我。”那个带子越来越紧,束在我的身上,几乎使我透不过气来。
难道是美丽的幻象落实了我的丑恶,美丽的幻象安妥了我的丑恶?
红的玫瑰,黄的玫瑰,蓝的玫瑰,在我的周围飘浮,盘旋。我迷醉于赤身裸体躺在她怀中的那种感觉,长时间一动不动,任凭她把一些水撩在我的肩头,然后,用手在上面轻轻地揉搓着。我想过拉一件浴巾盖在身上,却不知为什么,终于一动未动。
“我的名字叫薛荔。”她的眼睛很大很美,带着某种忧伤。
听着听着,我慢慢地蹲下去。我全身都在瑟瑟发抖,就像多年之前,我蹲在小瘪三家对面的屋顶上一样。
我看到了一个恐怖而真实的景象:我的内心世界被人刨开了,像一个被刨开的荒坟,亮出里面的累累白骨。我怯懦地、慌乱地对自己说:“不,不,不能这样,我要把它们立即埋藏起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