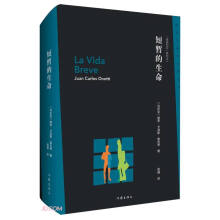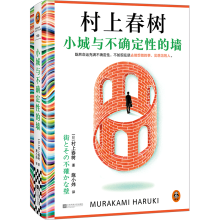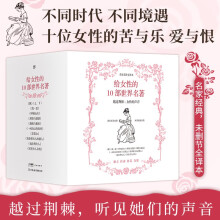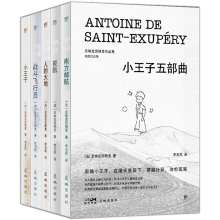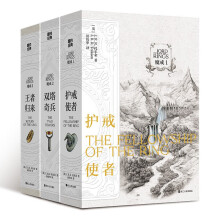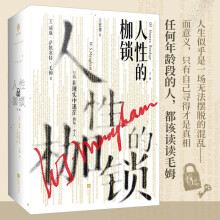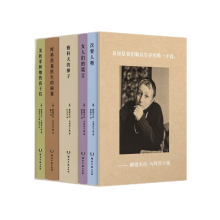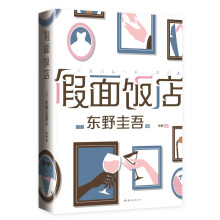走下列车时,我的鞋跟一绊,右脚卡在列车和站台间的缝隙里,人就跌倒了。在站台等着挤上车的人群里,我摔了个马趴。爬起来的这会儿工夫,他们都在周围推推搡搡争抢着上车。我还没站稳,只见有个人快步朝我走来,虽然那时我还茫然不知所措,可也马上注意到他善于运筹帷幄,能力出众而且反应迅速。我又差点摔倒了,此时他一把抓住我,这样一合力我倒进他怀里,始终抓牢手提包的那只手钩在了他脖子上。我笑出声来—明明是一声惨叫,却还能笑得出来。他的脸和我靠得很近,看上去颇有魅力,又不乏睿智。身手那么矫健有力,想必人会粗犷些,可看他的面容,却远比我预想的要秀气—恐怕也只能用“秀气”这个词来形容。他面露微笑,一副好奇不解的神色。我解释道:“我是写言情小说的。”他稍稍一愣,旋即会意地大笑。随后我起身站到他身边,抚平衣服,恢复了常态。
我们相互打量,对眼前所见之人甚是欢喜,也不加掩饰,但接着我就发现在他身后站了一个女孩,正注视着我们,距离近得让人不快,这个美妙时刻顿时烟消云散。见我脸色一变,他立刻回过身去看,对我说了声“你没事吧”就向她走去,拉住她的胳膊,把她领走了。我又一次注意到—这次是不无痛苦地注意到,尽管我得想明白,要细究这痛苦从何而来—他一照管起那女孩,就充满了责任感,他那称得上温文有礼的举手投足和无忧无虑充满活力的潇洒做派一下子消失殆尽,甚至连肩头的姿势都不一样了。
我站着目送他们远去。他会回头吗?没有。但那个女孩回头了,一脸狐疑,而且充满了敌意。他的情人?
年轻女孩往往恋上帅大叔。照我估摸,他五十几岁了。同龄人啊……我慢慢踏上台阶走出站去,内心的震撼出乎意料,可不仅仅是摔这一跤闹的。我想,那个人真是非比寻常,不管身处何方、置于何等人当中都会出类拔萃。你忘了多数人是多么平庸无奇,然后眼前就突然一亮。他又是怎么看待我的呢?好吧,我心里明白,那可不会有错。
到了街上,只见白云肆意掠过湛蓝的天空,阳光时隐时现,四月就这样昭显春光。四月一到,欧洲北方随便哪里都是好去处—短短两天前,我在马德里的时候便是这么想的。我同意为杂志社越发频繁地出差。他们说,女人上了年纪往往闲不住,爱四处走,总是逮着机会就出去玩。不过我坚称自己只不过人到中年,才不是上了年纪。唉,情绪着实低落。所幸我没有若无其事地去上班,而是回到家,打电话跟他们说今天不去了,明天吧。
要不是昨天外甥女吉尔那一通宣告,压根就不会出这一系列状况。我在图腾汉厅路站下过几千次车了?不数了,没什么好数的。我可曾在那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摔倒过?
昨天我从马德里回来,发现公寓不比往常那样如文件柜般井井有条,反而四处都是衣服。吉尔焦躁不安,苦着脸唉声叹气。我一下子全明白了,都快要号啕大哭起来了。就是这么伤心欲绝,因为直到吉尔真要走了的关头,我才知道她的离开会让我如此心痛。
“什么时候走?上哪儿去呢?”我问道。
“哦,简,我早该知道,你马上就能看出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问为什么呢。”
她说:“我要搬去和别人住了。”
“男的还是女的?”
“你认识的,马克。那个摄影师。”
“原来是马克!”
她马上紧张起来:“你不喜欢他吗?”
“吉尔,我只管要不要选用他拍的照片,其他都不管。从没想过他可能成为外甥女婿。”
“我可没说要嫁给他。”
“你妈妈会怎么说?”
“我在意的是你怎么说。”吉尔轻声道。我跌坐下来,竭力保持常态。她伫立在窗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窗帘没拉上,她身后的天空瞬息万变,漫天的白云,想必是给月光点亮了。马德里可是一轮圆月当空,这里怎么会不一样呢?我又想着如今自己有多么喜欢她。她站在那里亭亭玉立,身段苗条,因为这些日子保养得当,显得非常漂亮。她这么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我早该想到她在谈恋爱。让周围每个人都脸上有光,吉尔就是有这等本事。
我的脑子在飞速运转。既没有任何外来干扰,也没有任何不祥征兆,我为什么心烦呢?哪里出问题了?一切都各得其所啊。三年前,吉尔到伦敦城里来找出路,她老于世故的坏姨妈公然不避讳裙带关系,帮她在《莉莉丝》杂志谋到一份工作。吉尔在《莉莉丝》茁壮成长,承担所有事务,而且样样都拿手。她性格随和又体贴入微,作为一个好寓友,应付她难以捉摸的姨妈很有一套。她结交朋友,打了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预防针,不过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她给自己找了个年轻男友,想要和他共同生活。还能有什么故事比吉尔的经历更励志呢?
“吉尔,”我说,“我会万分想念你的。”
说完我哭了起来,吉尔也是。起先是一边哧哧擤鼻子,一边不好意思地哂笑,接着缓缓淌下痛苦的泪水,最后抽抽噎噎啜泣不已,我们相拥抱头痛哭。
“啊,简姨妈!”吉尔哭喊着。
“啊,吉尔!”
“你还不愿我住这儿呢,一开始的时候。”她嗔责道。
“我真够傻的。”
我们分开,轻拍慢打了好一会儿,总算不哭了。她煮好茶,我们俩喝了起来。看得出事情还没完。
“怎么了?”
“简,你想到没有?我一搬出去,凯特就会找上门。”
她那双大眼睛在浅灰蓝色的眼影衬托下呈现出偏灰的色调,目光炯炯,越过茶杯边缘紧随着我。我思索起这个问题来。凯特近三年来的境况是越发糟糕了。高级考试考砸了,又不肯顺从父母的心意再考一次。她请求我在《莉莉丝》杂志给她寻个差事,我说她得体谅我,在介绍年轻女眷进杂志社这件事上怎么着也得有个限度吧。不出所料,乔姬姐姐随即就给我打电话,说我肯定能有办法做点什么,我回答说:“你也知道,我让你女儿吉尔住在我这儿,照这样说来我做的可算不少了。”她说:“凯特觉得这很不公平,我得说,我们也都这么觉得。”
都是去年的事了。自打那时起,凯特就在家懒散混日子,考虑到底要不要学西班牙语。
想到最后,我对吉尔说:“我很清楚,一开始我并不愿意你来这儿住,结果我分分钟都过得很开心。不过凯特是不是真的和你大不相同呢?”
吉尔这人绝不敷衍了事,也不虚意逢迎。她没说“哦,一切都会好的”或者“她也不至于那么糟”之类的场面话,而是直接一语道破:“对,她很不一样,完全不同。你是不是真不了解我们俩之间的巨大差异?”
“大概是真不了解。虽说也见过好些给宠坏的孩子,把我们这辈人整得很惨。亲爱的吉尔,跟我真正一起生活过的年轻人,只有你了。”
“那好,我这么说吧,凯特的状态有点乱七八糟的。”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想问的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她坐在一把宽大的红色亚麻椅子扶手上,握着杯子陷入了沉思。
她一身白色便服,满头红发此时已经披散开来,因为回想着往事而眼神木然。她在回顾过去家庭生活中的场景。
“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生来就是如此?”
“对,有这样的。”
“要我说,恐怕我们家兄弟姐妹四个人就凯特会过得一团糟。”
“一辈子都挣脱不了?”
“即使真是这样我也不会觉得意外。”
“这话说得很重啊。”
“嗯,你在想,亲姊妹呢!她们从来合不来……没错,我们一向合不来。我能想到的糟糕光景就是和凯特一起度过的。一直都是那样。不过,我要说的是……”
“好了,我明白了。”
“你真明白了就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察觉到……人得有多坚强,才能受得了你!”
我因为一时过于伤感,叹息得有几分夸张,于是吉尔和我又开始了我们俩习以为常的笑闹,她说我多么容忍不了软弱,个性出奇坚强,我说其实是因为我不得不忍受她。“不,不,你听我说,”她接着说,“相信我,我心里很感激—不单是因为你让我住在这里,尽管这确实是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经历;也不仅仅是因为能进《莉莉丝》—如果我说现在我知道了自己在哪儿都能干得很好,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忘恩负义。
《莉莉丝》才明白了这一点,但我要感激人的是你,因为你从不让任何人得手,不曾让我……嗯,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她顽皮地浅浅一笑,不外乎是情境使然,海水般湛蓝的大眼睛急切地盯着我。
”我说。
她随即拥抱了我,就上床睡觉去了。
我独自多坐了一会儿,心想不久以后我又是孤家寡人了。哦,我在意的并不是一个人。独处从未吓倒我,恰恰相反,我喜欢独处。尽管我不太愿意承认,但我还是会想念吉尔的蓬勃朝气,还有她的青春活力。
她真是轻岁月里的我。
在办公室里,我听他们叫她“契波芙”。我当时就纳闷,为什么给她起了个俄国绰号,这个活力十足的英国姑娘哪里像俄国人了?结果发现我弄错了,他们是叫她“其婆附”:有其姨妈必有其外甥女。吉尔刚到这儿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样子,但她时刻警醒,悟性又高,打定主意要住下来跟着简姨妈学本领。她往往也会一时消沉,产生倦怠。
那时候她终究还是她自己,还是吉尔……不过很快她就变成了我,带有我的个性、我的仪态、我的投足,发出的是我的声音。
一开始我并没有看出来,听了绰号才恍然大悟。然后我想,理所当然的事嘛!我以她为镜,在她身上观察自省起来,总体感觉有点受宠若惊,自忖道:嗯,我这人—准确点说是我当年,还算差强人意嘛!但再看看其他方面,思绪又开始起伏转变……这孩子相当能干,
一举一动都那么准确无误,经过了精心揣摩,不过是不是拿捏得稍许过火?其机智与优雅,天资之聪颖—我从来不曾拥有,或者说不觉得自己拥有,恐怕现在依然欠缺。她似乎一走进某个场合,就能够,或者说想要掌控局面。简而言之,就是好管事儿。她开口很有分寸,语调轻松诙谐,有时候语带机锋,暗讽情况荒谬或者处理不当。她说话给人的印象是,在她看来,人世是一出喜剧,总体令人快活。但是她这副姿态是经过一番修炼形成的习性,她自己对这一出喜剧并没有那么确信。她声音中的每一音符,每一音高,每一抑扬,每一顿挫,无一不是我。
此外,吉尔生性略为固执,甚至是故意显得钝讷,让人产生一种自满的印象。可事实果真如此吗?难道这不是她努力要证明自己实力的结果?难道不是她面对重重困难,勇敢无畏地迎头而上、全然忘我的结果?她是不会承认的,哪怕是对她自己。
由此引发了一些很有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吉尔为什么不选择诸如她父母亲那一类颇受尊重的人来作为榜样?假如真存在那么一些个得到一切权威认可的楷模,那我所能想到的最合乎标准的人选就是乔姬姐姐和她的丈夫汤姆了。假如课本所言无误,那吉尔是不是在投奔我之前,应该早就已经“内化”了其一其二或者已将二者兼收并蓄?可实际上并没有,她引以为榜样的,竟然是她整个童年都听闻其自私和浅薄的简姨妈。
第二个问题,我也思考已久了:过去的吉尔是那样的怯生生、迟疑不决,如今人们看到的吉尔俨然游刃有余,那么和男朋友马克坠入爱河的吉尔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后的吉尔将会是简姨妈的翻版,将来大家想到的、谈及的,也都是那样的她。
第三个问题:我效仿的又是谁呢?我全然不像自己的父母,尽管我尊重他们,但不得不说,他们不成风格,缺乏让人注目的力量,埋没在人群之中。不,可能我在吉尔这个年龄,在进《莉莉丝》工作之前,我也崇拜原来部门的某个人,后来才成为别人崇拜的对象。正如人们所见所知,三十多年来,从简娜·詹姆斯到婚后的简·萨默斯,都以其精心打扮、光彩照人、优雅自信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这可是门艺术!我甚至自问,当乔姬姐姐数落我的肤浅以及种种不是的时候,说不定她是指我青春期到后来随性发展所形成的、在她看来不切实际的个性。有必要向她问个清楚吗?至于她,则早就从动作到语调再到习惯各个方面
都“内化”了我们的母亲。
现在吉尔要走了,她每一步都走得很对。我坚信她以后也不会走错,不会缔结不幸的婚姻后经历崩溃,到中年变成怨妇。我对她很有信心。
没错,她肯定也会来探望我,我在办公室也能见着她,我们会是朋友。但毕竟和现在不一样了。
好了,趁早放手,简娜。趁早放手,简。
过去就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