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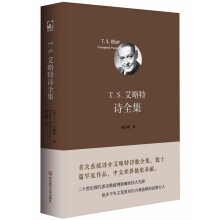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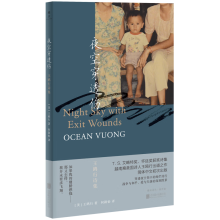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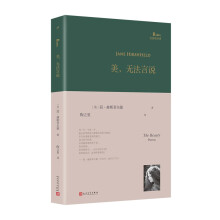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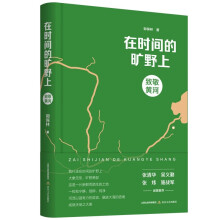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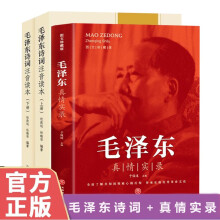
寻获心灵的空间
六十年代初次见它,
我驾驶着大众露营车
同行中有一位癫狂的同性恋诗人和
一位嗓音沙哑,迷人却爱冒险的女孩,
从加拿大驱车南下
我们行驶在山脉干旱的东部。途经大古力峡谷、
蓝山、熔岩流洞穴,
穿越阿尔沃德沙漠—那儿叉角羚成群—
澄亮耀眼的黑曜石铺成的
土渣路,直通维亚镇,
适逢九月末,道路难辨,
拂晓霜浓;而后
沿峡谷而行,陡然显露出
边际蜿蜒的银色平原
哦,啊!
空观
萌生出满心的慈悲!
我们沿着干盐湖的边缘
驶向小路尽头的酒吧
从烟溪沙漠边,
越过山隘,进入金字塔湖畔,
顺着印第安巫师的帐篷之路
途经他们修建的一片大牧场。
次日,我们终抵旧金山
此时此刻,世界似乎
正步上一条新的道路。
七十年代,再一次从
蒙大拿州驱车回家,我索性驶离高速公路
碾着一条土渣小路,驶向平原,
车陷抛锚—孩子受惊—只好露宿一夜,
次日,故障解除,继续上路。
十五年飞逝而去。八十年代
携着爱侣,我来到路尽之处。
整日山中跋涉,
在荡然无存的旧景中四处寻觅,
发现一条小径
石碑上刻满铭文,掩映在山艾树丛中
“踩踏贪念”
“人生极美之物非物也”
此乃一沙漠先贤遗世之语。
高坡俯瞰,海岸线渐隐渐现,
拉洪坦湖早已消失,
割喉鳟精灵藏匿淤泥里—
哥伦比亚猛犸象的骸骨
堆积四百英尺高,风化在波浪侵蚀的
海滩岩礁上;弯角的
沙漠羊的轮廓铭刻岩石里,
开着卡车转奔干盐湖
驶向那未知之地,
骨灰色的尘土翻滚飞扬,
驰骋数英里,来到无迹无形之地,
车子沿岸滑行,缓缓停下
在这干涸龟裂
平坦坚硬的地面上,
冬天,雪花螺旋般飞舞,
夏天,骄阳窑炉般炙烤。
离开这无名之地,离还是不离,
平等、至远、无界。
万籁寂无声,
无水、无山、无
灌木、无草,
因为无草
无荫而唯有汝影。
不平缘于不不平。
不增不减。故而—
路上空无一物!
—天即是地
地即是天,
两者无间,只有
飒飒微风,
吹入帐篷口,
时间静止于此。
我们心心相印,
艰难盘坐,
亲吻彻骨。
黎明阳光直耀眼睛。
远处齿状山峰,名叫李尔王。
一晃进入九十年代,一个沙漠之夜
—昔日恋人已成吾妻—
故友、旧车,大家聚拢一起;
孩子们骑车嬉戏,车轮巨弧隐现黑暗中
黑灯瞎火—唯有金星闪烁
在那花萼般的新月旁,
众享锅中的烤蚱蜢。
大家蜂拥而至—
儿女围绕成圈
吃着蚱蜢,扮着鬼脸,
荒野中为昆虫吟经诵唱,
—野性,在这
傻乎乎的可爱空间
盈满心房。
走中走,
脚下 大地在转
溪山无尽永不停歇。
百万年船
百万年船,
晨光之船,
航行在青绿的无花果树林间,
黎明的白色荷兰货船
隐现于红海中—红色烟囱—
越过我们的邮轮,驶向拉斯坦努拉,
太阳早已炙烤我的肩胛骨,我
跪在破旧的钢甲板上,凿下斑驳锈漆。
海上茫茫,唯见灰色的T-2旧邮轮和一艘
白色荷兰货船,
太阳圣船,
神鱼阿伯特与亚特,
嬉戏于船头波浪中,
咸咸红海
船首劈波斩浪
海豚疾速潜行,阳光下
在前翻后滚的浪花里
飞驰旋转,身影交织
哲人德日进戏谑而言:
“牢抓星球之舵柄”
海豚领航,我们直驶晨曦。
——北岛
对原始部落的喜爱与尊重,给予大地的荣光,从城市和工业离开——进入过去,以及可能的沉思、人群……斯奈德的诗背后有着这样的意识和承诺。
——英国诗人格林·麦克斯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