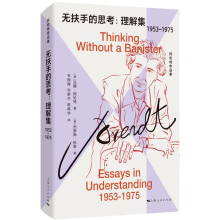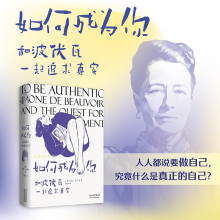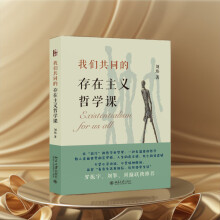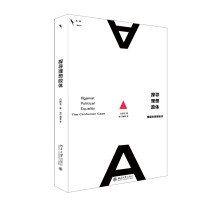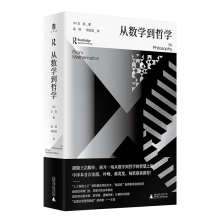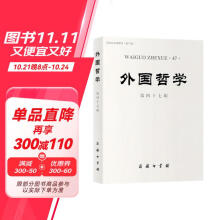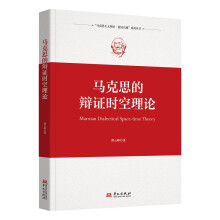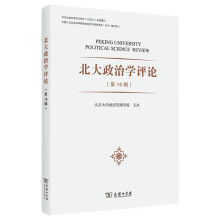汤一介先生(1927—2014),湖北省黄梅县人,生于天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56年起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书院、什刹海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代表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大部分著作与论文已结集为十卷本《汤一介集》出版。主编有《汤用彤全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与李中华共同主编)、十一卷本《中华佛教史》(与季羡林共同主编)等著作。以古稀之年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