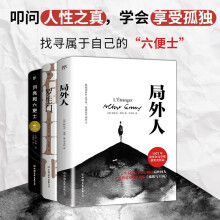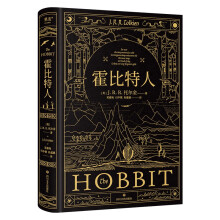《在人间》:
大师兄在女顾客面前,双膝跪地,动作麻利地张开手指,给女顾客测量鞋子的尺码。他两只手直哆嗦,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那女人的脚,好像生怕把她的脚碰坏了似的,而女顾客的脚非常的肥,活像一只倒放着的歪脖瓶子。
有一次,一位太太抖动着她的一只脚,缩着身子说:“哎呀,您弄得我直痒痒……”“这是出于对您的礼貌。”大师兄急忙热情地解释说。
他缠着女顾客的那副模样,看着真叫人觉得好笑;为了不笑出声来,我转过身去,面对着门上的玻璃。但我非常想看看他是如何揽生意的——大师兄的手法太使我感到可乐了,但同时我又想,我永远也不会这样彬彬有礼地张开手指在顾客的脚上量尺码,也不会这样麻利地把鞋穿到顾客的脚上。
有时候,老板常常离开商店,到后面的小屋里去,而把萨沙也叫过去;这时店里就只剩下大师兄和女顾客两个人了。有一次,他的手触摸到了一位褐色头发女人的脚,然后他就把那几个手指头攥在一起,在自己的嘴上吻了一下。
“哎哟,”那女人惊叹道,“你真够调皮的!”他却鼓起腮帮子,使劲发出接吻的声音:“啧——啧!”这时我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我前仰后合的,伸手去抓门的把手,结果把门给拉开了,门上的玻璃也被我的脑袋撞破了。大师兄气得冲我直跺脚,老板用他那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头直敲我的脑袋,萨沙则使劲揪我的耳朵。晚上回家的时候,他严厉地对我说:“这样老板会把你赶走的!喏,这有什么好笑的?”并且解释说:要是太太们喜欢大师兄——生意就会好做一些。
“即使那位太太不需要买鞋,但为了看一眼她喜欢的店员,也会买上一双的。这你就不懂了!真让人替你操心……”这话我很不爱听——没有谁关照过我,更不用说他了。
每天早上,那个病病歪歪、脾气很不好的厨娘,总是比萨沙早一个小时先把我叫醒;起来后,我得把老板一家人、大师兄和萨沙的皮鞋擦好,把他们的衣服弄干净,把茶炊摆上,给所有的炉灶预备好木柴,再把午餐时用的饭盒洗刷干净。到了店里,我便扫地,擦灰尘,准备茶水,给顾客们送货,然后,回家取午饭;这时守店门的差事就由萨沙替我来干;他认为这活儿有伤他的尊严,便骂我说:“笨蛋!要别人替你于……”我感到烦闷与无聊,我过惯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从早到晚,一直在库纳维诺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在浑浊的奥卡河岸边。在田野和森林中游荡惯了。这里没有外婆,没有伙伴,没有人可以说话,然而生活却使我感到愤愤不平,它让我看到了它丑恶的、虚伪的一面。
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女顾客什么东西都没有买便走了——这时,他们三个人会有一种被人欺弄的感觉。老板将自己甜蜜的微笑装进了衣袋,命令道:“卡希林,把东西收起来!”接着便开始骂骂咧咧:“呸,这头母猪,鼻子拱到这儿来了!在家里坐得无聊了,跑到商店里闲逛来啦。你若是我的老婆,瞧我不把你……”他老婆人长得很干瘦,黑眼睛,大鼻子,经常冲他跺着脚,大声吆喝,像对待用人似的。
他们经常一面鞠着躬,一面说着恭维话,彬彬有礼地将熟悉的女顾客送出店门,然后便恬不知耻地对她大加诋毁,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我真想跑出去,追上那女人,把他们背后议论她的话告诉她。
我当然知道,人们一般背后都互相说坏话,但他们几个人是无人不说,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好像他们是被什么人认定的几个最优秀的人物,他们的使命就是来评判世界的。他们对任何人都感到嫉妒,从未夸奖过什么人,对每一个人,他们都知道一些他的短处。
有一回,店里来了一位年轻女人,面色红润,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身上穿一件黑毛皮领的天鹅绒斗篷,其容貌在黑毛皮领的衬托下简直就像一朵奇妙的鲜花。她从肩上脱下斗篷,递到萨沙手上,这时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了:浅灰色的丝绸衣裙紧紧裹着她那苗条的身材,耳朵上的钻石在闪闪发光——她不禁使我想起了聪明美丽的瓦西里萨①,因此,我相信她就是省长夫人本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