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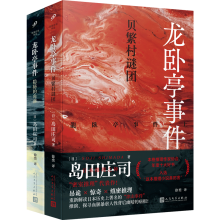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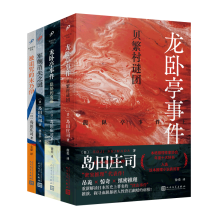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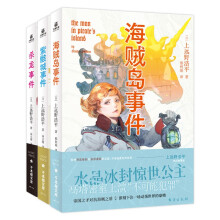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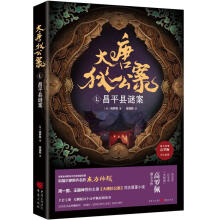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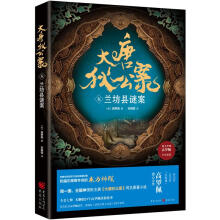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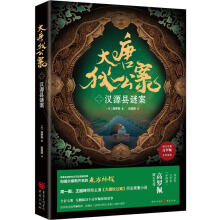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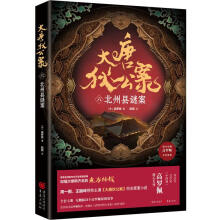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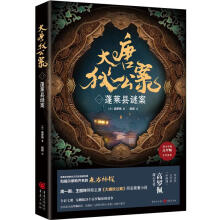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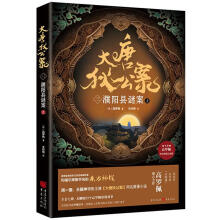
托尔斯堪称奇特的作品。
人类文学上描写死亡的*的神作。
小说对婚姻、情欲、伦理、死亡的探讨具有惊人、无与伦比的现实感。
名家名译,译笔优美动人,完美展现托尔斯泰风格魅力。
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选,包括两个短篇《克罗采奏鸣曲》、《魔鬼》和一个中篇《伊凡·伊里奇之死》。这三个中短篇分别是关于婚姻、爱欲与死亡的主题,围绕着婚姻、家庭、伦理、情欲与死亡,具有有非凡的震慑人心的魅力。
《伊凡·伊里奇之死》被认为是人类文学上描写死亡的*的神作,是托尔斯泰晚年一部重要的代表作。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法国作家莫泊桑深深为之折服,曾经感叹说:“我看到,我的全部创作活动都算不上什么,我的整整十卷作品分文不值。”
《克鲁采奏鸣曲》上流贵族情感忏悔录,托翁(据说是本人写照)扮演奥古斯都、卢梭,讲述了一个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互相怨恨的贵族夫妇,因丈夫认为自己对妻子拥有类似物主的所有权,因此并不尊重妻子,而频频与妻子发生争吵,后来在丈夫对妻子狂烈的性嫉妒中杀死妻子而后反省、忏悔这种肉欲结合的婚姻关系的故事。是托尔斯泰*奇特的作品,当年发表后,俄国审查官只允许发行普通人难以承受的高价版本,美国邮政禁止邮寄刊有《克莱采奏鸣曲》连载的报纸。
《魔鬼》则探寻了人性中的情欲。它认为人是无法控制这种欲望的,无法摆脱,直到欲望对象的毁灭或自己的毁灭。小说对情欲的巨大力量以及其与理性道德的激烈冲突的描写是摄人心魄、无与伦比的。
《克洛采奏鸣曲》
什么东西能阻挡他呢?什么也没有。相反,一切都在引诱他。而她呢?她又是什么呢?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迷。我不了解她。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动物,而动物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而且也不应该去阻挡它。
一钩新月,微微有点寒意,马好,路更好,车夫也和气,我乘车向前,感到心旷神怡,几乎完全忘记了等待着我的那件事,或者正因为我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才尽情享受,准备去与生活的欢乐告别。
要知道,这是很可怕的,我居然认为自己对她的肉体拥有无可置疑的、完全的权力,就好像这是我的肉体似的,与此同时,我又感到我控制不住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不是我的,她可以任意处置它,而且她并不想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处置它。
我记得有那么一瞬,仅仅是一瞬间,在我把刀子捅进去之前,我可怕地意识到,我正在杀死一个女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我的妻子。
我转过去头去望了一眼孩子们,又望了一眼她那被打伤的青肿的脸,我才第一次忘掉了我自己,忘掉了我的夫权和我的骄傲,我这才第一次发现她也是个人。我这才感到,那使我受到侮辱的一切——我那整个的妒忌心,是如此渺小;而我所干下的事情是如此重大,我恨不得把脸贴到她的手上说:“饶恕我吧!”但是我不敢。
《魔鬼》
她系着一条白色的绣花围裙,穿一条红褐色的方格裙子,头上扎一块鲜艳的红头巾,光着脚站在那儿,怯生生地微笑着,显得那么鲜艳、健康、美丽。
叶甫根尼远不是个好色之徒,他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他自己认为是不好的事他觉得很苦恼,他从来也不觉得心安理得,甚至在第一次和斯捷潘妮达幽会之后,他就希望从此不再看见她。但过了一段时候,驱使他去干这种事的烦躁不安的心情又出现了。
突然,情欲在他身上猛烈地燃烧起来,仿佛有人用手揪住了他的心。
可是不论他走到哪里,不光是心里想着斯捷潘妮达,而且她的活生生的形象到处追逐他,简直使他难忘掉她。
上帝呀,他在想象中把她描绘得多么迷人呀!
他知道,不管在哪里,只要和她迎面相遇,又是在黑暗中,只要可以和她接触,他肯定会放任自己的情欲。
他每天都想想出一些办法来摆脱这魔鬼的诱惑,而且这些办法他都一一使用过了。
他瞟了她两三眼,感觉到又有点不对头了,可是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第二天,当他骑马到村子里的打谷场去,毫无必要地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接连不断地、充满温情地看着他所熟悉的那个年轻女人富有魅力的身影,这时他才感到他已经毁了,完全地、彻底地毁了。又是那种痛苦,又是那种笼罩一切的恐惧。无可挽救了。
《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他:有时候,在经过长时间的痛苦之后,他最希望的是(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能有人像可怜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他真希望别人能像爱抚和安慰孩子那样地来爱抚他、吻他、为他而哭泣。
他觉得,他被塞进一只又窄又深的黑口袋,而且被越来越深地塞进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
二十年永远是老一套,而且越往后越变得死气沉沉。正如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却还以为自己在步步高升。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大家看来,我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却从我的脚下一步步溜走了……终于时候到了,你去死吧!
他置身于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有许多朋友和家人,可是他却感到一种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海底还是地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独。
整整三天,在这三天中,对他来说时间已经不存在了,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他塞进一只漆黑的口袋,他在那只漆黑的口袋里挣扎着,就像一个死囚明知他不可能不死,可还在刽子手的手下苦苦挣扎一样。
他寻找他过去对于死的习惯性的恐惧,可是没有找到。死是怎样的?它在哪儿?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也没有。
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啊!“
译者序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克洛采奏鸣曲
魔鬼
伊凡 伊里奇之死
1.托尔斯泰堪称奇特的作品,当年发表后,俄国审查官只允许发行普通人难以承受的高价版本,美国邮政禁止邮寄刊有《克罗采奏鸣曲》连载的报纸。
2.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看了此书后说:托尔斯泰是个性变态者。
3.著名俄罗斯文学译者、诗人、学者汪剑钊教授,小说家赵松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