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灾难冬夜
这是一个多日来难得再听到两派人打枪的冬夜,一阵妇人撕心裂肺的哭声打破了旷野的沉静,把终南山下颜家河畔沉睡的小村庄从凄冷中惊醒了,使睡梦中的人们一下子睁圆了惊恐的眼睛。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颜蛋他大不在了!”
于是,村里的男女老少,裹着破棉袄,趿拉着不遮脚后跟的烂棉鞋,吵嚷着,拥挤着,一窝蜂似地涌向了颜家。
一间破旧的小土屋霎时挤满了破衣烂鞋的众乡邻,乱嘈嘈一片。名叫柳秋桂的主家妇人坐在炕上停尸门板的顶头,呼天抢地地哭叫着,如天塌了一般。
乡邻们同情地抹着眼泪,议论纷纷,唏嘘不断。
“家里没了顶梁柱,这一大家子,让一个女人领着这么多娃可咋过呀!”
“是啊,才四十刚出头就没了男人,秋桂这日子以后啥时能熬出个头啊!”
五岁的小祖倩睡在小屋旁边油毛毡搭建的棚屋里。吵闹声把祖倩惊醒,睡眼迷蒙中,她摸黑穿着散发出棉絮腐臭气味的棉袄,却怎么也摸不着棉裤,她急得“哇”一声大哭起来。凭感觉,她感到家里出大事了。听到哭声,比她大六岁的姐姐祖香进来,沙哑着嗓子,摸索着给她边穿裤子边吸溜着鼻涕说:“咱大没了。”刚说完就又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大,大,我要俺大……”祖倩来不及勒裤腰带,两手提住裤子大哭着跑出了棚屋。小女的哭声惊得满屋子的人忙让开一条路。祖倩扑到炕上停尸的木门板上哭得眼冒金花。她知道,自己从此就再也见不到大了,再也不能被大驾在脖子上追云撵鸟了。越哭越伤心,娘一把将她揽在怀里,又放大了悲声。
母女的哭泣把满屋子的人感染得泪水涟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人红鼻肿眼,啜泣声仿佛要顶开破旧房屋上的屋顶。
早已成家另过的颜家大儿子颜耀祖,前脚一跨进门,就“大”的一声趴在停尸土炕边上哭起来,众人忙上前扶劝。颜家老三颜耀昭拨开人群,从屋里头冲上来,鼻孔喷着怨气,双眼瞪得滚圆,质问老大:“你干啥吃的?早些时辰做啥去咧?大临咽气时还唤你呢。”
见老三双手叉腰,两眼喷着气愤的火焰,要打人的架势,老大的蚕眉动了几下,自知理亏地嘴里嗫嚅着:“今儿轮我看饲养室哩……”
大伙忙好言相劝,说耀昭,现在不是论理的时候,安排商议老人安葬的事要紧。老三强咽下怨恨,咬紧的牙关把腮两边撑得又鼓又硬。
村民们按照乡规习俗帮助颜家办理丧事。主事的安排村人去亲戚家报丧,本家轮流和逝者的儿女们守尸,离本族血系远一点的则送两张黄麻纸,表示对逝者的安抚,对活人的慰藉。守尸的儿女万不可离开一步,要轮换着看守。听大人说,这尸体万一被猫或老鼠之类的东西爬上身,就会出现惊尸现象,说是一旦惊尸了,死人会突然坐起来,抱住跟前的任何一个活人,直到把活人吓死,也掰不开死人的双膊……有了这种传言,谁家死了人都会精心看护,从不敢有半点马虎。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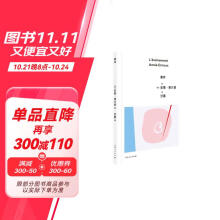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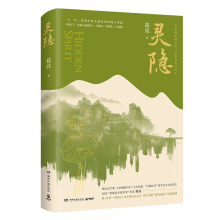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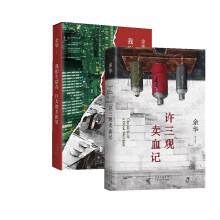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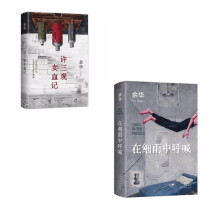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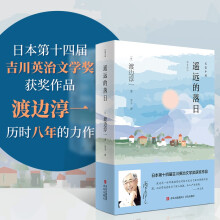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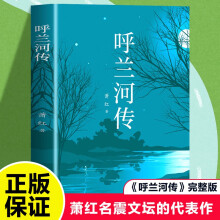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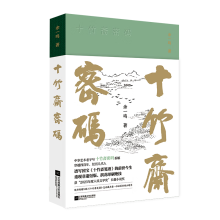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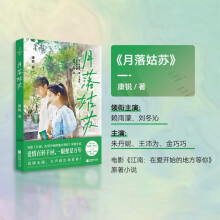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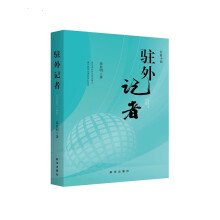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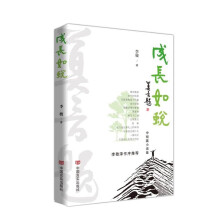
《终南山》立足于现实,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四、五十年嬗变前后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状况和价值取向与追求,它将城市与农村、社会与家庭、传统道德与现代思想碰撞交织在了一起,将灵与肉、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跨度几十年的以终南山地为核心的社会风俗图,使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社会时代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了一起,用玄妙的艺术手法对物象、天象等自然征兆进行了巧妙的植入,让读者去感悟,去破解谜底,可见林仑的功底是深厚的;她的作品是反映的普通民众的传统思想和精神物质的追求,反映的是大众的现实生存状况和喜怒哀乐,因此,它是贴近人民群众的,也是大众欢迎的!
——贾平凹
作家林仑走笔串线,不仅在《终南山》中铸就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魂魄,塑造了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真实地记录了近半个世纪我们民族的发展史,而且还匠心独运,集艺术、哲学、玄学于一体,集自然的人文的神韵于一身,在关注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上为人们留下了深沉的思考。坦率地讲,《终南山》应该不愧为一部史诗般的作品,它是我们民族一段历史缩影的情景再现,它更是中华文学艺术的一块瑰宝,它恢弘深沉的文学思想,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思索和回味。
——成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