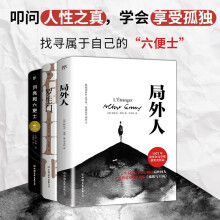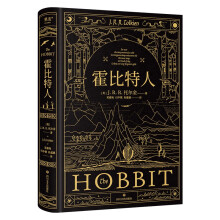这件事儿只能发生在英国,别处就不行。在这个国家里,可以说,人跟海洋打成了一片——海洋跟大多数人结了缘;一般人不是完全懂得,也懂得一些儿海洋上的消遣、海洋上的旅行,或者海洋上挣面包的生涯。
我们这几个人围着红木桌子坐下来。酒瓶,红葡萄酒杯,以及我们的脸(当我们用肘拐撑住的时候)都在桌面上反映出来。一个是公司董事,一个是会计员,一个是律师,一个叫马洛,还有我自己。
那董事从前在“康威号”上当过水手,会计员在海上干过四年;律师——一个可敬而顽固的保守派,高派教会[1]的信徒,一个最好不过的老头儿,有德行的君子——曾经在“英国轮船公司”的船上当过大副,当年邮船至少有两支桅杆扯起横帆(此外还高高低低地张了好些辅助帆),往往乘着一阵和顺的季节风,直航到中国海。大家都是在商船上谋生,所以海洋,还有同行的友谊,把我们五个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什么热心于乘游艇、荡船以及这一类的玩意儿所能建立的,因为一个只是生活中的消遣,另一个却就是生活本身。
马洛(Mafiow)——至少我想他是这样拼写自己的名字的,给大家讲了一个航海的故事,或者不如说,讲了一段航行史:
“是的,我也见过一些东方的海洋,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到那里去的航行。你们几个都知道,有些航行仿佛老天特地安排好来说明人生、作为生命的一种象征的。你奋斗、苦干、淌汗,几乎拼上了命,有时候可真拼掉了命,只是为了想要千好一件事,结果还是不行。这并不是你的过错。你就是什么也做不成——大事也罢、小事也罢,总之世上没有你能做成的事——就连娶一个老姑娘,或者把可怜巴巴的六百吨煤运到指定的港口都办不到。
“那次航行从头到尾都是件值得纪念的事情。那是我头一次到东方去航行,又是我第一次当二副,又凑上我的船长第一次带船。你们得承认这可是一宗难得的巧事儿。船长少说也有六十岁了,是个小个子,腰背宽大,却并不十分挺直,肩膀向前弯,有一条腿往外曲得厉害。他有一种庄稼汉所常有的歪来扭去的古怪模样,脸儿就像一副胡桃钳子——下巴尖跟鼻尖几乎碰在一起,把陷进去的嘴巴遮住了。脸儿四周嵌上一溜铁灰色的绒毛般的须发,有些像洒上煤屑的棉织品围巾。在他那张老脸上有一对蓝眼睛,活像小孩子的眼睛,流露出坦白的神情——有一种十分平常的人,凭着天生难得的纯洁的心灵和正直的胸怀,一直到死都保持着的坦白的神情。他怎么会挑中了我可难说了。我本来在一条走澳洲的上等快船上当三副,那时候刚离了职。他对于上等快船似乎存着一种偏见,认为太贵族化,太时髦。他跟我说:‘你知道,在这条船上可得工作啊。’我说我一向到哪一条船,就在哪条船上工作。‘啊,可是这里的情况不同,而且你们这班从大船出来的先生们……好吧!我敢说你行。明天就来吧。’
“第二天我就去了。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我才二十岁。时间过得多么快!那一天也算是我生平最快乐的一天了。想想吧!第一次当二副——一个真正负起责任来的职位!就是给我一大笔钱也不能叫我抛掉这个新职位。大副仔细地把我打量了一下。他也是个老头儿,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他长着一个鹰鼻,留着雪白的长胡须,名字叫‘马洪’(Mahon),不过他硬说他这个名字应该念做‘曼恩’(Mann)。他有很好的亲戚,可是命运总是不好,所以从来也不曾得意过。
“至于船长,他多年来一直都是在沿岸来往的商船上,后来在地中海的商船上,最后进了走西印度群岛的商船。他从来没有绕过好望角。他勉强能写几个字,可是根本就不想写什么字,这两个当然都是本领到家的海员,夹在他们两个老头儿中间,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孩儿跟两个老爷爷在一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