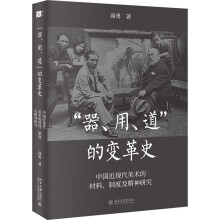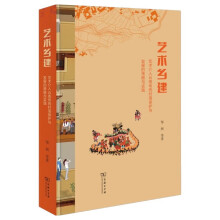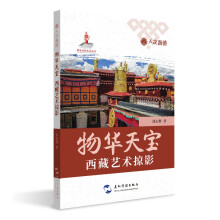开机那天
2015年5月20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前一天晚上,我特地去理了个发,洗了个澡,清清爽爽,睡了个好觉。早晨起来,看看天有些阴,穿个短袖还有些凉。不由添了三分忐忑:天公不会今天犯病,来捣蛋吧?
开车行进在秦岭脚下的环山公路上,一路绿色,天空却阴沉得发灰,老天爷不知道跟谁吊脸。我坐在车里,心绪空洞茫然,不知想些什么,不知该说些什么,闷着。竟然错过了上白鹿原影视基地的路口,往返回来,竟然找不到上原的路了。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九点半才到达外景地,谁见我都说就等你了。我说,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老天一数,还少一难,于是让我迷路了。
仪式是在白鹿原景地进行。一边是戏台,一边是祠堂,一段土墙中间一个拱门,围成了一个乡村的场院。面朝西摆了香案,制片人小彪悄悄告诉我,昨天已经专门到水陆庵烧了香,请人算好了,今天九点半到十一点半是吉日吉时。场地上站满了剧组人员和前来祝贺的朋友,原计划6月我们还要举办一个隆重的开机新闻发布会,今天本想悄悄地开机,没想到还是来了这么多人。《白鹿原》魅力大呀。
十点钟,简单仪式开始了,导演刘进代表剧组,已经装扮成白嘉轩的张嘉译代表演员,我代表投资商讲了话,都有几分感慨,仿佛背负了《白鹿原》的沉重,心头沉甸甸的有了分量。开始烧香求天保佑了,剧作的演职人员都参与进来,每人手持三炷香,虔诚地冲着东南西北一一拜着,大香炉被香满了,青烟袅袅。
白鹿原终于开机了,从2001年7月23日与陈忠实老师签下第一份改编合同,至今已经整整15年了。这15年,《白鹿原》像一个梦魇,缠绕折磨着光中影视的同人们,浸淫其间,咂摸不出滋味究竟是苦是乐。放弃和坚持的情绪轮番来袭,期盼和焦躁的心态反复煎熬,鼓励和疑问始终在周围氤氲。以致有一段时间,听到“白鹿原”三个字,就心头发紧,然后就一阵莫名其妙的惆怅,或伫立,或默坐,久久不能释怀。一种沁入血液的茫然,拌和着一种宿命式的乐观,卯上了,豁出去了,上了贼船就看谁命硬了,闷头熬吧。
有记者问我,说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要15年后才能投拍,你还坚持吗?我不知道。说15年,是回眸掐指一算的结果。而日子是一天一天过来的,一个红萝卜始终在眼前不远的地方挂着、晃着,逗着你跟着、跑着、蹦一蹦、跳一跳,总够不到,急火火左右地踅摸着,生怕别人半路截和。过来了,往事成了回忆,就开始发酵了,有点酸涩,有点美妙,有一份酒意,别有一番滋味,闹得老想掐自己是不是梦还没醒。申捷经常安慰我说,大剧有大剧的命。
我看着香冉冉燃尽,香灰奇怪地向外围弯曲,形成了一个大大的花朵,不掉不落,蔚为奇观。我本想招呼众人看看这一番奇景,忍住了。大家都在紧张地准备拍摄第一个镜头,我默默地注视着,全当是上天异象,表示对我们的祝福吧。
开机的第一场戏是白嘉轩和鹿三驾车归来,全场安静地等待,只有工作人员一溜小跑地忙碌着。突然,太阳破云而出,瞬间阴郁的灰暗一扫而空,天空阳光灿烂。十一点了,突然一只公鸡叫起来,引吭高歌地来了三声。激动的申捷一个劲:我×,我×,真他妈吉祥,大中午的公鸡打鸣,太阳露脸。开拍令喊起来了,场内安静。鹿三驾着马车从村外的拱形门洞里走进来,经过生活体验的演员熟练地驾着马车,白嘉轩斜靠在车帮上,一只脚踩在车辕上,叼着烟袋锅,一阵青烟飘起。赵军给我说,他看了时间,开拍第一个镜头,十一点十七分,还在吉时。我暗中心头一紧,“11.17”,正是我的生日数字。又暗自笑了,一件事揪心太久了,人就有些神神道道,开始信命。
《白鹿原》开机了。站在白鹿原上,放眼对面,秦岭苍茫起伏。思绪怎么也整理不到一块。满脑袋都是碎片式的片段……申捷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他说老赵,我把白灵写死了,我难过得哭了一夜……第一次和张嘉译谈《白鹿原》项目,他一脸凝重:“赵总,咱都是陕西人,《白鹿原》可不能在咱的手里糟蹋了……”开机前和导演刘进闲聊,他说,这个组,聚集了一批有梦想有野心的人,全都飚上劲了,这一点太难得了。这剧成了……2010年10月,《白鹿原》电视剧立项获批,我和陈忠实老师找了个酒馆,喝了几盅,陈老师说:“《白鹿原》改编,我就指望电视剧了。”……一段一段,蒙太奇的视频,飞来飞去,在脑海里飘飘荡荡。
终于开拍了。申捷历时三年呕心沥血,给电视剧提供了一部让人感叹的优秀剧作,先有了三分底气;这么一批优秀的演职人员全像打了鸡血,憋足了劲,就有了七成把握,各级政府领导全力支持,天时地利人和,全了。熬过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期盼和焦虑,熬过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折磨和苦恋,怀孕五月,坐胎已稳,摸着渐渐隆起的肚皮,享受着小精灵的骚动,开始琢磨那幸福美妙的时刻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白鹿原》火遍全球荧屏。”嘿嘿! 第一天的戏顺利拍完了,剧组吃开机宴,在白鹿原下一个宽敞的农家乐里,快乐而又疯狂。频频举杯,各种理由,各种祝福,酒不醉人人自醉,闹腾到晚上十一点。回家的路上,大雨骤然倾盆而至。看着暴跳的雨点在雨刮器的来回中迸溅,暗自窃喜,剧组已经进入梦乡了。老天有眼呀!
一定要折腾出一部感天动地的大剧来,一定要拍成电视剧史上的里程碑,一定要让同行们觉得没有糟蹋了好东西,一定……突然,有人推我,说到家了。我愣愣神,在车上睡着了?看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美梦成真还待时日,加油啊,伙计们,拜托了。百年修得同船渡,让我们珍惜这一份同呼吸共命运的缘分。
云翻麦浪
白鹿原上,长着粮食,活着人。
原上绿油油的麦田。一垄一垄的,从田地的这头,整齐地排列到田地的那头。有风吹过的时候,挨着土黄色的田地,会有一条流动着的从青黄到浅绿再到深绿的涟漪。涟漪熟了,就成了黄灿灿的 麦浪。
都是丰年就好了。细细的麦秆顶着性感饱满的麦穗,自己个儿摇着,或者互相咯吱着,再像约好了一样,向风的方向奔突。于是,天上,有云卷云舒,褐黄色的土地上,有云翻麦浪。
但不总是丰年啊!改朝换代、战争、饥馑、瘟疫、运动,这些说来就来的天灾人祸;爱了、恨了、情了、怨了、背叛了、逃离了、圆满了、堕落了,这些躲也躲不了的命运际会;像风一样,突然就呼啸而至;像云一样,突然就诡谲蔽日。
白鹿原上,不好活人,人不好活。
所以,白嘉轩说,要在这原上活人,心上要能插得住刀子。
头发花白的白嘉轩带领村人祈雨,大喊:“吾乃西海黑乌梢”,烧红的钢钎从左腮穿到右腮,佝偻着的腰杆瞬间直戳戳地挺立着。在原上活人,这是白嘉轩的姿态。同样的时刻,鹿子霖跳上方桌,浑身扭着,双臂也扭舞着,大口吹出很响的气浪,当他去接那只筷子粗细烧得通红的钢钎,却一下子软了。看透他的冷先生说:你就是差些白嘉轩的 硬气。
交农事件,鹿三在流水一样涌泄的人群里大喊:“白鹿村鹿三算一个。”这一喊,让这个话不多,只是老实本分做事,一门心思地忠于东家的影子般的存在活成了人。“去杀一个婊子去除一个祸害”,鹿三,于月亮沉落后,走进小娥的破窑洞,对准小娥的后心,刺进了磨好的铮亮的梭镖钢刃,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壮举。在白鹿原上活人,得有这种不明就里不分对错的愚忠,得有不管对象不问来由的侠气,得有不会害怕也不能后悔的豪狠。
庄稼一季一季,麦子一茬一茬,人是一辈一辈。
白秉德老汉、鹿泰恒老汉,还有祠堂里坐在方方正正的太师椅上的那些方方正正的老汉们,如同割了麦子以后所剩的麦茬,终会被犁铧翻进生养的土地,成为下一季麦子的土壤,变成下一辈人的养料。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是在仙草生下孝文的那个当口,听到白嘉轩在他的耳边亲口说出“咱白家有后了”,又用微弱的声音嘱托过“白鹿白鹿,有白又有鹿,才叫……白鹿原哩,要守住这个原”后,才放心地撒手人寰的。与白秉德老汉争斗了一辈子的鹿子霖的父亲鹿泰恒,手里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的高坡之上,看远处斗了一辈子的对手白秉德老汉的长长的送丧队伍,没有喜悦,眼睛里有的只是知音已去的苍茫悲凉。
在白鹿原上活了一辈子人,白嘉轩、鹿子霖也毫不例外地白发苍苍了。那个白鹿村里的秋千架,那个白鹿原的少年们曾经尽量荡起,想要对外面的世界一探究竟的秋千架,被两个老人扶起,秋千架上坐着新生的白鹿原少年。历尽千帆,白嘉轩和鹿子霖,白鹿原上曾经的新麦,也在等待自己生命中的犁铧,然后,心甘情愿地被犁铧翻进土地里去,成为土壤,变成养料,让新麦长成,看云翻麦浪。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