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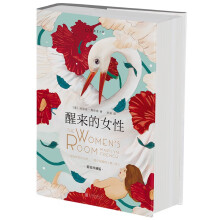









祖与占都爱上了同一个女子:聪明貌美的凯茨。
在这样的关系中,占选择了成全温柔单纯的祖。他们一起到乡间度假,度过了美妙时光。
然而一战的爆发,却让他们失去了联系,德国人祖和法国人占成为了敌人,他们多么担心会在战场上杀死自己的好友。
战争结束,祖与占再次相遇,凯茨毫不掩饰对占的爱,这段三角关系平衡而快乐的维系着……
三个美丽女子
为了先做安排,祖比占早八天到达慕尼黑,他在这儿住过两年,邻近着这三个女子。
他在朴实的人家那儿为占租了两大间房,并向他的三个女友宣布占的来到。他对每一个人评论占的方式是这么不同,以至于她们三个交换这些评论时,并不以为是同一个人。
占一到,祖就介绍黎那让他认识,她知道关于那大理石桌子的事。
让祖吃惊的是,甚至在茶点未结束之前,黎那,这个狡黠漂亮的女孩,已和占互相同意以下几点:
(一)占很不同于祖对他的描述。
(二)黎那也几乎不像大理石桌上的素描。
(三)两人感觉很好,但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他们一致声明期待中的一见钟情并没有如愿发生。
“我多么羡慕两位的利落与果断!”祖说。
至于绿西和杰特薇德,祖在城里最摩登的酒馆里,在晚餐时刻,一次把她们给了占。
当她们脱下了她们的外套时,显出了对比效果。她们坐在浅色的木头桌子旁边,桌子上铺了桌巾,摆上奇怪的杯子。
一抹幸福腼腆的微笑流露在祖的嘴角,他告诉另外三人,他们都在他的心上。是一阵宽裕的懒散气氛,没有任何不适。
占自言自语地说:“您是怎么办到的?祖,把两个如此不同又如此……的女人聚在一起!”
他找不到形容词。是沉默为他发出了那两个字:美丽。
她们都领会到了。
祖因快乐而脸红,他想要回答,杰特薇德扬手制止他并且说:“祖是我们的知己,我们的导演。他有强大的想象力加上天使般的耐心。他把我们写进他的小说里,他安慰、嬉耍、追求我们,但从不强制我们。他只不过忘记了一件事:他自己。”
“多么美好的赞词!”占说。
“所以他一呼唤我们,我们就来了。”绿西说,轻微地抬起头。
祖用他有趣的方式说起计划中的黎那和占的约会失败。这事黎那已经给她们打过电话。
杰特薇德说:“理所当然,他们是不合适的。黎那是被惯坏的小孩,占先生不会喜欢的。”
祖问:“那他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呢?”
“我们会知道的。”绿西不带表情地说。
这是她的低沉的嗓音第二次传到占的耳里。坐在两个女人中间他觉得为难,他真希望他的眼睛可以一直个别地又同时地看到她们。
这开始得像一场梦。
不久祖以他强大的组织能力,为大家安排了一个节目。为了一劳永逸地取消先生女士小姐等等客套称谓,他们将以博爱的名义喝他们最喜欢的酒,而且为了避免传统姿态以及考虑手臂间的勾搭太过醒目,他规定所有喝酒的人的脚都必须在桌面下互相接触。果然节目就这样进行了,祖被快乐所鼓动,很快地移动自己的脚。
有好一会儿,占的一只脚触着杰特薇德的脚,而另一脚挨着绿西的脚。绿西的脚首先慢慢移开了。
绿西是哥特式美女,有椭圆而长的头颅。她处理每一件事都从容不迫。她的每一个时刻,不管是赋予别人的,或是给予自己的,她都以同等完整的价值看待。她的鼻子、嘴巴、下巴带着省城式的骄傲;小时候在一些宗教节庆里,她曾是她那类风格的代表。一个大布尔乔亚家庭的女儿,研习绘画。
杰特薇德三十岁,是希腊美女,天生的运动员。她不经训练就得过滑雪比赛的奖章。她从行驶中的电车跳下来毫不费力就可完全站定。她让人想见识她的肌肉。她的儿子四岁了,没有父亲,她不相信父亲这回事。她靠彩绘木雕过日子,生活时好时坏。她是贵族,但被她的阶级所放逐,幸而有一班艺术家尊敬她、宠爱着她。
这个晚上像迂回曲折的河流一样流着,所有的存在发出共鸣,一些火苗开始萌发。他们有这样一些共通点:对金钱相对的不予重视,以及对于持续不断处于上帝掌中——杰特薇德宁称之以魔鬼的——的意识。
祖话多得恰到好处,但是,午夜两点,他开始对灵魂以及人的处境有点太过娴熟,又挑衅地讲了一些大胆的笑话,可能他在私下里怯于冒险的,都借着这些公开的言论赢回来了。他拿他的两个女朋友开玩笑,拿他自己开玩笑,几乎也要开起占的玩笑。他难道不是替他们开启了一道乐园的门,他自己却不确定进得去吗?他难道有预感吗?他开始对永恒的天父做那些冗长的重铸世界的建议时,他那融合敬意与喜悦又不时带着利爪的方式令人难以忍受。
显而易见的,祖是个美妙的朋友,但却是个意志薄弱的情人和丈夫。他自己亦是一再怀疑,而他借滔滔不绝的言论掩饰。
“祖坏了这个晚上!他总是这样。”杰特薇德遗憾地说。在祖起身跑去找流动摊贩买纸烟的时候。绿西点头,带着纵容。
最后十五分钟在祖的胡言乱语里结束。他不让别人有说话的机会,坚持制造那些拙劣的气氛。他的三个朋友为他感到痛苦,他们想要再次见面相聚但不要他在场。
占还不曾认识祖这一面,但一想,他也确实曾在他们的谈话里感觉到一些痕迹。在那些一对一的谈话里,在那些美丽女子不在场的时候,祖在自己的宏论里是飘荡着飞扬着的。
把她们分别送到家门口以后,祖与占在一个大公园里走着。天亮了,祖已经安静了下来。
“多么不同凡响的晚上!”占说:“多么胆大豪放的两朵奇葩!多么神圣而又凡俗的爱……我不会很乐意同时再看到她们两个的……”
“我懂您的意思。”祖说:“哪一个更让您印象深刻?”
“我仍然晕头转向的。”占说:“我并不急着想要知道。您呢?祖?”
“绿西,我求过婚,看样子我还得再求一次。当绿西拒绝我的时候,杰特薇德可以安慰我。我曾经带杰特薇德和她的儿子到意大利海边旅行。她只给我她的身体,没给我她的爱……您知道吗?占,当我遇见绿西时,我很害怕,我并不想任凭自己被爱牵着走。但她在登山时伤了脚,她让我治疗她的脚,包扎又解开那绷带。我希望那脚伤永远好不了。”
“我认得她的手。”占说。
“是我自己好不了,”祖接着说:“当她复原以后,我大胆地自我推荐做她的丈夫,她说:‘不——’那声音那么温柔,使得我想再听一遍。”
001 序 一个诗人的电报体爱情小说
021 对话夏宇:我为什么翻译《祖与占》
029 祖与占
111 凯茨
199 直到尽头
我所认识的、Z美丽的当代小说之一,是亨利-皮埃尔•罗什的《祖与占》。这小说叙述的是两个朋友与他们共同爱人之间的故事,幸亏有一种再三斟酌衡量过的、全新的美学式道德立场,他们终其一生,几乎没有矛盾的温柔的相爱。
——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
所谓电报体,那些节省的抑制的退却的句子,由无数的句子删掉后剩余的句子,用许多句点完成的节奏,就像鼓点一样在绷紧的皮面与皮下的空洞产生共鸣,放弃一般小说着力的心理分析以及前因后果重大转折的铺陈,只写表面而且心甘情愿停在表面……
改编电影与原著的天作之合,小说与电影都让对方更加灿烂。
——诗人、翻译夏宇
喜欢《祖与占》的都是爱自由的疯丫头,将来会到处跑,没有一个男人能拴得住她。
这样的疯丫头也有为追逐的爱情停留脚步的时候。
——张小娴《收到你的信已经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