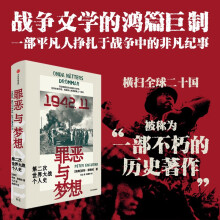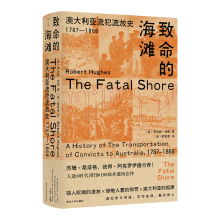导 论 图像的证词
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
———库尔特•塔科尔斯基
本书的主要内容关于如何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二:一是鼓励此种证据的使用,二是向此种证据的潜在使用者告知某些可能存在的陷阱。一两代人以来,历史学家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兴趣,涉及范围不仅包括政治事件、经济趋势和社会结构,而且包括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等。如果他们把自己局限于官方档案这类由官员制作并由档案馆保存的传统史料,则无法在这些比较新的领域中从事研究。
出于这一原因,范围更加广泛的证据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除了书面文本和口述证词外,图像也占了一席地位。以身体史为例,画像可以用来说明人们在关于疾病和健康的观念上发生的变化。如果要证明衡量美貌的标准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阐述过去的男人和女人都看重个人外表的一部历史,画像是更为重要的证据。此外,如果没有图像提供的证词,后面第五章所讨论的物质文化史实际上无法进行研究。正如第六章和第七章试图说明的,图像提供的证词在心态史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见中的不可见性?
很可能,目前的状况依然是历史学家没有足够认真地把图像当作证据来使用,因此最近的一次争论就是围绕着“可见中的不可见性”的话题。正如一位艺术史学家所指出的,“历史学家……宁愿处理文本以及政治或经济的事实,而不愿意处理从图像中探测到的更深层次的经验”,而另一位艺术史学家所说的“以屈就的态度对待图像”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使用摄影档案的历史学家人数相当少,相反,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依然依赖档案库里的手抄本和打字文件。历史学的专业杂志很少刊登图片,即使杂志同意刊登图片,愿意利用这一机会的作者也很少。即使有些历史学家使用了图像,在一般情况下也仅仅将它们视为插图,不加说明地复制于书中。历史学家如果在行文中讨论了图像,这类证据往往也是用来说明作者通过其他方式已经做出的结论,而不是为了得出新的答案或提出新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已故的拉菲尔•塞缪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他如何发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摄影照片。他在文章中把自己和同一时代的社会史学家称作“视觉文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作为一个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孩子,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完全属于前电视时代的人”。他在中小学和大学接受的教育都是训练他如何解读文本。
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确有为数极少的历史学家已经把图像当作证据来使用,尤其是那些研究书面档案非常缺乏或根本不存在的历史时期的一些专家。例如,如果不使用阿尔塔米拉和拉斯科的洞穴绘画作为证据,确实很难写出欧洲的史前史;而没有陵寝绘画作证据,古埃及的历史将显得极为贫乏。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实际上,图像是有关狩猎之类的社会实践的唯一证据。有些研究较晚时代的历史学家也非常认真地对待图像。例如,研究政治态度、“公众舆论”和宣传的历史学家很早以前就使用照片作为证据。此外,近半个世纪以前,研究中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戴维•道格拉斯曾明确地指出,贝叶挂毯是“研究英格兰历史的主要史料”,“应当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描述以及普瓦提埃的威廉所做的描述相互参照,放在一起加以研究”。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