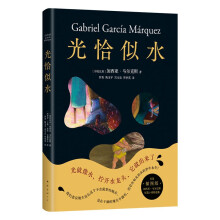阿兵的身后拖着叮当叮当的回声,回声清脆而悠长,搅扰了礼士胡同午后的寂静。这种响声跟寺庙里和尚敲磬差不多,谁会想到它是脚步声呢?然而礼士胡同的人知道这是瘸子出动了——多少年来礼士胡同的青石板路面总是在这个时候被阿兵的拐杖撞疼,拐杖的顶端为了耐磨镶嵌着钢垫子,它们在地面上叩出像花瓣一样美丽的伤痕,如果在晚上,肯定还会吐出一朵一朵的火星儿。胡同里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这是他们午休时的一种伴奏。
就连胡同的狗也被这种声音磨厚了耳茧。阿兵路过大墩家时,大墩的红毛狗就横卧在路心上,对阿兵的到来不理不睬,根本没有让路的意思。其实这条狗是很怕人的,地处交通路口,人见人打,早就被打得没了狗性,即使一声粗壮的咳嗽,也会吓得它夹紧尾巴开溜。阿兵用拐杖戳戳它,它竟然连头都懒得抬,只翻开白眼瞟了一下,很不屑的样子。这狗也不肥,在别人就一脚跨越了,但阿兵不行。他只得费劲地从它身边绕过去。过去之后阿兵有些窝火,回过头朝它呸了一口,没想到这狗应声跳将起来,呼呼往前扑,生气地汪汪狂吠,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
吓得阿兵往后连跳几步,险乎摔倒。看见瘸子可怜见的,红毛狗似乎有点不忍,呜里乌拉含糊其辞地抗议了两句,又躺倒睡觉了。狗的气消了,这才轮到阿兵生气:难道我就活成了这样,连狗都瞧不起我?
人瞧不起他可以容忍,谁叫自己少一条腿,跟别人不一样呢?胡同里的人明里暗里把他当怪物,水莲看他的眼神就跟看她家的那只三脚猫一样,那只猫早几年不知怎么被老鼠夹子夹断了一条腿,一直半死不活的。有人怜悯这算好的,阿兵最怕像大墩那样的衰人当面羞辱他,大墩经常模仿他走路的样子,边学边嬉皮笑脸地嚷嚷,嘿,像不像鸭子划水!他们都瞧不起他,整个胡同的人,这他知道。正因为这样,阿兵每次要出门都选择午后,这时整个胡同都沉入了酣梦,基本上没有人影(阿兵也曾尝试过在深夜出门,结果没走几步就摔破了膝盖,没有路灯的胡同充满了陷阱)。
然而他躲过了人,却没想到碰上了狗。一只瘦里巴叽的癞皮狗,也敢不把他当回事!
阿兵的气愤是可想而知的,这样,下面发生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买鞋。阿兵对柜台后面正在打盹的女售货员说。他现在是在街道上的一家鞋店里,趴在他对面的售货员睡得很实腾,口水窜了出来,把腥红的唇膏冲开了一道豁儿,在腮帮的脂粉上犁下几条不规则的深沟。售货员动也不动,就像刚才的红毛狗一样不理他。阿兵有些来气,他提高声音吆喝了一遍,售货员一个激灵吓醒了过来,瞪着他说,喊什么喊,随便从货架上摸出了一只鞋,扔在阿兵面前。阿兵说我不要这种,他用手指着一种棕色的皮鞋,那种鞋的帮儿上钉着一颗黄铜五角星,煞是好看。鞋被抛了过来,阿兵试了一下,太大了。
要35码的,阿兵说。大概是这样的小脚男人太少了,售货员翻遍了好几个货架,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最后她撅着屁股,挪开了货架下面的几只废纸箱,好歹掏出一只35的,扔给阿兵。阿兵立刻推回去,说我要左脚的。这下一直觉得自己很能忍耐的售货员终于发火了,她说你这人有病吧?左脚右脚还不一样试!到现在为止,售货员还没有发现阿兵是个残疾人,因为柜台遮住了阿兵的下半身。
我就要左脚的,你听好了!阿兵瞪着售货员,硬梆梆地回应道,你不就是一个卖货的吗?售货员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横的顾客,她在国营商店当太岁可是习惯了的,这倒激起了她的好奇心,她重新打量着、并且是认真地打量着阿兵,把头探出柜台,似乎是要看看阿兵是不是三头六臂。
哈哈!她兴奋地叫了起来:你是个瘸子,哈,瘸子!
瘸子瘸子瘸子!这称呼像锥子一样连续扎在阿兵心上,他鬓角的脉搏蹦蹦跳,右腿的断茬口像被撒上了辣椒面一样尖锐地刺疼。阿兵正想发作,但他最终却没有发作,作为残疾人,阿兵知道自己是弱者,他经常得靠智力而非蛮劲来维护尊严。在那天的午后,阿兵很快地就想到了一个报复的恶作剧,他觉得设一个圈套让这个胖女人钻比臭骂她一顿更有趣也更痛快。
阿兵问这鞋多少钱,售货员说八十四块。给,他把四十二块钱甩在柜台上。售货员数了一下,说:你有没有搞错?阿兵说怎么啦,售货员说什么怎么啦?钱不够!阿兵说,你是白痴,不会算账吗?阿兵这一骂,把那个售货员骂愣了,她当下还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阿兵笑着说,一双皮鞋八十四,一只皮鞋是多少?
售货员醒悟过来了。我看你才是白痴,皮鞋有单卖的吗?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阿兵问。
瘸子!
瘸子是几只脚?
一只。
那就对了。你知道我只有一只脚,你也同意卖给我皮鞋,那你肯定是卖一只皮鞋给我喽!
售货员被问得张口结舌,真不知道怎么被这个瘸子给套住了。天下明明没有鞋子单卖的道理,可她却理屈词穷。
阿兵笑了,他说,谁让你骂我瘸子的?骂人不能白骂,另外的四十二块钱你贴上吧。
售货员急了,她一把拽住那只皮鞋说,我不卖了!
说得容易,阿兵不放手,屁放出来你能一口吞回去?
争吵声引来了不少街上的闲人,他们围在鞋店门口。这时,从鞋店后面走出来三个男人,他们是库房送货的。售货员急忙向他们嚷嚷,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三个男人中的一个大胡子看着阿兵轻蔑地笑了,嘿嘿,臭虫也成精了,快掏钱!
那个男人狗熊一样壮实,整整高过阿兵半个身子,阿兵心里有点怯,再说他也确实不占理。但阿兵不愿轻易示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已经掏过钱了。
那是一只鞋的钱!
我就买一只鞋。
行!那个男人说,他抓住阿兵的手,只轻轻一拧,阿兵拿鞋的手就松了,大胡子把那只左脚鞋没收了,塞给阿兵一只右脚的。笑着说,瘸子,满意了吧。另外两个男人也一脸坏笑,快试试吧,他们说,你的右脚呢?
阿兵无可奈何地盯着这只右脚鞋,他不能说不要,因为他说了要买一只鞋的。大胡子是在耍他。然而阿兵一想,也行,右脚我不能穿,可左脚那只鞋你们不也得贴钱吗?他暗自得意,这起码是打了个平手。可是很快大胡子又反悔了,他在把那只左脚鞋放回货架时发现了上面的脏手印子,就将它往阿兵的怀里一塞,说,你的爪子印,全归你了,掏钱吧!
我不要!
你掏不掏?大胡子一把抢过了阿兵的拐杖,阿兵摇摇晃晃地差点摔倒了。另外两个男人上来左右一夹,把阿兵夹在了中间。
阿兵害怕了,他的手哆哆嗦嗦地伸进口袋摸索着钱包,然而就在这时,不知道怎么的,他忽然发现了围观人群中的一双熟悉的水泡眼,那双水泡眼由于高兴,鼓凸凸的都快要弹出来了。那是大墩。大墩后面那个露了半个鸡窝头的女孩好像是水莲吧,她是不是又抱着那只三脚猫到兽医站去看病?阿兵忽然硬起来了。他知道这会儿不能熊,熊了以后在礼士胡同他就连红毛狗都不如了。
我不掏!
算你嘴硬,大胡子说,你别仗着是个残疾人我就不敢打你,我有的是治你的法子。他说着就把阿兵的拐杖斜戳在地上,一抬脚就准备往上踩。他大象一样粗的腿足足有三百斤吧。
阿兵是没有办法了,他知道硬撑下去的结果是今天自己从这里爬回去。大胡子男人扎足了势等着阿兵告饶,但没有反应,最后他只好狠了心往下踩。就在他的脚快要落下的一瞬间,忽然,“呱!呱!”两声清脆的竹板声响起在人群里中,紧接着是快板书:
哎,哎,叫大哥,您别发火,
那只皮鞋卖给我!
大家伙都回头朝后瞧,人堆里挤出了一个人:嘿,又一个瘸子!
瘸子继续说着快板书:
嘿,您说得对,说得好,
我是瘸子没有错。
两条腿的人满地跑,
一条腿的才是宝!
哟,这瘸子的嘴!大家都给逗乐了,连大胡子也不知不觉地松开了阿兵的拐杖。瘸子蹦达蹦达地跳到阿兵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
叫兄弟,您受难为,
瘸子买鞋得配对儿,
您左腿,我右腿,
合作起来是绝配。
这时候大伙儿才注意到,这两个瘸子果真是一左一右。天底下竟有如此凑巧的事!
不过,大胡子有点怀疑。这瘸子拄着两根竹竿做拐杖,竹竿的一头劈开撑成“丫”字形夹在胳肢窝,比起阿兵从商店里买来的那种,它们只能叫劈柴棒。他的衣服已经分不清颜色了,因为斑斑点点的什么颜色都有。以这种颜色为背景,映衬着他脖子上拴着的一面小锣、左肩斜挎的一只海碗大的腰鼓和右肩斜挎着的一支毛瑟枪一样的二胡。他是流浪艺人?靠卖唱混个半饥不饱的人还能买得起皮鞋?
不过瘸子的鞋确实烂得不像话了,鞋帮像张开的牛嘴。大胡子看他时,他故意让脚指头在烂茬口里探头探脑,仿佛牛伸出舌头舔嘴唇。
大胡子有些迟疑地把那只右脚鞋从阿兵怀里抽回来,塞给了瘸子,他也乐得有人给他台阶下,不然欺负残疾人怎么说也不算光彩的事,是要落人话柄的。瘸子分三次从兜里掏出皱皱巴巴的一大堆钱,全是角角分分的零票子。售货员厌恶地捏着鼻子,用元珠笔拨拉着数钱。
围观的人们不高兴了,他们好不容易等来的一场戏让这多事的瘸子给搅黄了,大墩吆喝道,不要卖给他,乡巴佬!就在这会儿,数钱的售货员叫道,嗨,瘸子,你的钱不够,差五块!
不会的,不会的,我刚才在外面数过了。
难道老娘昧你的钱了?你自己过来数!
瘸子老老实实地自己过去数了一遍,数完了结结巴巴地说,怎么……会……怎么……?他的脸涨得通红,汗水都急了出来。
看热闹的叫道,打这个东西,敢到咱们地界来骗人!阿兵从兜里掏出了一张崭新的五元票子,拍在售货员的面前。够了吧?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按说阿兵应该感谢瘸子给他解围。阿兵也是这样想的,但他却做不来,瘸子口口声声自称“瘸子”,让他反感:别人轻蔑倒也罢了,为什么还要自虐?阿兵庆幸刚才有五块钱的机会,让他还了瘸子的人情。他宁愿相信瘸子是真的要买鞋,与他配对是事出凑巧,谁也不欠谁。
观众们带着没有尽兴的遗憾骂骂咧咧地散出鞋店,阿兵也随在人后。可是瘸子却拽住了他,他说大哥,您别走,我还没有还您的钱呢。阿兵想这瘸子搞什么鬼,有钱为什么刚才不拿出来?正琢磨着呢,瘸子又“呱,呱”敲响了竹板:
嗨嗨,叫大伙,都别走,
还有好戏在后头。
瘸子武艺十八般,
样样都让您开眼。
大伙还真的让瘸子给拉住了,反正这小镇上也没有什么娱乐,他们正发愁如何打发这星期天午睡之后的无聊。大家就地围成一个圆圈,像观看耍猴一样把阿兵和瘸子围在中间。鞋店的那个大胡子男人不干了,他吆喝道,喂喂,出去,出去,都出去,我们还营业不?但女售货员乐意,她说别价别价,我还想看呢。
阿兵真觉得自己成了猴子,他甩开瘸子的手,叮当叮当从圆心走到了圆边,围观的人哄笑着说,嗨,不要走,一左一右,天下绝配!阿兵生气地从人堆中挤了出去。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离开,远远地站在敞开的鞋店门外看着瘸子的表演。
瘸子向大胡子男人讨一张椅子,大胡子不给,他只好把一半屁股搁在鞋店的门槛上坐下来。瘸子先操起锣当当当敲几声,然后说:各位老少爷们,大家有钱的帮一个钱场,没钱的帮一个圆场,兄弟我献丑了。随着一阵急促的颤音,瘸子演奏起了二胡名曲《江河水》,然而他还没拉两句,就被大墩粗暴的声音打断了:停了停了,什么声音呀,锯木头一样难听!瘸子换了一首通俗歌曲《涛声依旧》,仍然是刚拉了几下,那个女售货员说话了,她撇撇嘴,糟蹋毛宁哩,帅哥的歌怎么能让瘸子拉?大胡子男人朝瘸子吆喝道:喂,瘸子,你还有没有别的把戏,光拉锯我可要赶人了!
这时候阿兵看见瘸子扶着拐杖缓缓地站了起来,猛地吸了一口气,忽然松开两支拐杖,在身体即将栽倒的一刹那间,双手撑在地面上,人整个倒立起来。瘸子的面色憋得紫红,好像一只熟过头的茄子,宽大的衣服褪下来拥在脖子上,亮出瘦骨嶙峋的胸膛,汗水一疙瘩一疙瘩地在那里翻山越岭往下滚。就这样,仍然没有人施舍哪怕一分钱。瘸子气喘吁吁地说,各位爷们,还不……过……瘾?那我就再来一个绝的:倒立……舞蹈。
瘸子真的用手支撑着身体在地上跳起舞来。
这是仑巴……
这是探戈……
这是恰恰……
……
瘸子声嘶力竭地报着曲目。
阿兵觉得自己全身的肌肉抽得紧紧的,骨头也发出了嘎巴嘎巴的响声。他不能再看下去了,再看下去他准会疯。
阿兵挤进人堆里,把五块钱狠狠地摔在瘸子的面前,然后含着眼泪离开了。
他听见瘸子在后面喊,大哥,大哥,借你的钱还没还呢,怎么还能要你的钱?但他没有回头。一个人怎么能这么没有尊严呢,哪怕是残疾人!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里阿兵一直在寻找工作。他原来是玉器加工厂的工艺师,现在下岗了,厂里效益不好,裁了12个人,名单上排在第二的就是他。阿兵之所以要买新皮鞋,就是为了在应聘时让人家看着精神一点。其实阿兵平时是不穿皮鞋的,收入不高手头拮据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更让阿兵伤心的是,一旦到鞋店买鞋,新鞋拿到你手里时,在别人,马上就会急不可待地穿在脚上去享受履新的快感,而在他,却是当即给你一个打击:提醒你是一个残疾人,是一个缺少零件的残次品!
新鞋并没有给阿兵带来好运。现在肢体健全的人都纷纷失业,谁愿意要一个残废呢?哪怕他是一个精神抖擞的残废。今天阿兵就去了参加了一次招聘会,那是这座小城的另一条街道招聘公共厕所管理员,所谓管理员是客气的叫法,干的活实际上就是坐在茅房外面收屎尿钱,时不时进去冲一下茅坑。阿兵想这下贱的事该不会有人抢吧,稍微看得起自己的人谁愿意戳在厕所门口闻臭气呢?然而到现场一看,嗬,人山人海的他挤都挤不进去,只好打道回府。
现在阿兵就垂头丧气地走在礼士胡同里。午后的蝉鸣粘涩而沉闷,一群灰色的鸽子扑楞楞低空从阿兵的头顶飞过去,落在不远处一道长满芨芨草的同样灰色的房脊上。阿兵的眼睛是茫然的,他的心里就像现在的礼士胡同一样空空荡荡。所以他不可能看见就在自己眼前的大槐树下面席地而坐的瘸子,或者说他可能看见了,但却毫无反应。瘸子大哥大哥叫了两声,阿兵仍直愣愣地往前走。瘸子就“呱”“呱”地打起竹板来:
叫大哥,你听我言,
小弟就在你面前。
你走路,别犯愣,
小心碰得头面肿
。
竹板的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像爆竹一样响亮,阿兵哦哦地反应了过来。瘸子说大哥,我找了你好几天了,光在这棵树下,我就坐了两天。找我干什么?阿兵淡淡地说。他不愿意和瘸子打交道,有点瞧不起他。瘸子说,给你还钱呀。我不要了,阿兵说。本来这钱也是他送给瘸子的,没打算让他还。可是瘸子不答应,他说我不能背着债过日子,你看,他笑着说,我背上的东西够多的了,要压死人的。他耸耸肩,铜锣腰鼓二胡咣当咣当响。瘸子把十块钱塞给阿兵,阿兵又把钱塞了回去,他们之间推来挡去的。
你拿回去!不知怎么的,阿兵忽然发火了,他猛地把钱摔在地上,声音和手指都是颤巍巍的,你……你是在糟蹋我……
瘸子被骂晕了,他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阿兵,阿兵也呆呆地看着他。足足有几分钟吧,瘸子开口了,他说,大哥,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你失业了,找不着工作,烦着哩,你骂我出出气吧。
阿兵无言以对。
大哥,瘸子接着说,我给你拉几支曲子听听吧?听曲子能败火。在家里,我爸发脾气,我就给他拉曲子,他听着听着就气顺了。
阿兵鼻子一酸,他觉得自己刚才过分了,不该给一个无辜的人发火,而且同样是一个可怜的人,甚至比自己还惨。阿兵把那张谁也不要的十块钱从地上拣了起来,最后决定去喝茶,两个人共同把它花掉。顺便也听听你的曲子,阿兵说。
他们来到了街上的悦来茶馆。这是一个老式茶馆,新的都叫“茶道”或“茶艺馆”,里面有一些很刺激的玩意,当然也很贵,阿兵只听人说过,从没有去过。阿兵是悦来茶馆的常客,以前他经常在这里消磨下班之后的孤寂和无聊。他们到的时候正是悦来茶馆的老顾客们在家午睡的当口,店里冷冷清清的,就连老板也趴在油光瓦亮的樟木桌上打瞌睡。
茶沏之后,阿兵首先问了瘸子的身世,瘸子告诉阿兵他叫阿水,老家就在离小镇不远的那个有着一条大河的县。那个县是非常有名的,阿兵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它,那里正在修一座很大很大的水库。阿兵奇怪为什么阿水对他的情况这么了解,阿水笑着我是卖唱的,我得不断地找故事,这样才能有说词呀。
阿兵想到了那天买鞋的事,他见识了阿水的一张嘴,那确实是一张出口成掌、饶有趣味的嘴。你的新鞋呢,阿兵问。他看到阿水脚上仍然穿着那只裂口子的破布鞋。
穿不上,阿水笑着说,小了一码。
……你……
阿兵的话渐渐地多了起来,多少天了,不,应该说是很多年了,阿兵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他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现在他把阿水当作知心朋友,而且,不知怎么的,阿兵竟然不能把持住自己,倾诉中越来越流露出深重的无助和悲愁。
你说怎么办,我找不到工作以后怎么活?
没事的。阿水笑着说,总会有办法的。
会有什么办法呢?谁会把一个残疾人当回事!
大哥,阿水说,别指望别人,我们得靠自己。
可我们是残疾人啊。
谁又不是残疾呢?阿水反问道,我们的残疾是肢体上的,看得见,有人的残疾在灵魂上,看不见,这世上有完美的人吗?
阿兵想一想确实是,连毛主席都犯错误呢。
阿水说,所以你不要太在意残疾,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不要把残疾看成是上天对人的惩罚,而看作是老天爷对我们的钟爱,他选中了我们,特别要考验我们的毅力和品质。古人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饿其体肤,苦其心志,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要担当大任的人!大哥,阿水乐呵呵地拍着阿兵的肩膀说,我们都是杰出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优势。
阿水像一个哲学家,说话云里雾里的,阿兵似懂非懂。但最后的几句他逮住了:这不是在自我麻醉吗?阿兵想。可是看着阿水乐观洒脱的样子,阿兵觉得阿水这样做也有道理,像自己这样整天忧心忡忡的,又能怎么样?
不要让残疾成为疮疤,一揭就疼。阿水说,那天你在鞋店里发火,我就觉得不值。第一,瘸子是一种称谓,它指的是单腿行走的状态,你不要把它理解成贬义的,别人这样叫我们,如果不是捏造,我们就不必生气;第二,即使别人是恶意的,我们也不必计较,因为我们是杰出的,不跟他们一般见识,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正是出于嫉妒才这样叫我们。
阿水的话正中阿兵的隐衷,他最恼火的就是别人拿残疾取笑他。现在经阿水这么一说,他多少有点脱敏了。为了彻底解除阿兵的条件反射,阿水连续地叫阿兵瘸子,瘸子瘸子瘸子!阿兵起先有些别扭,接着慢慢可以小声应答了。阿水鼓励他大声些,最后他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面对瘸子的称谓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