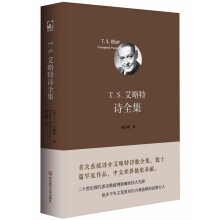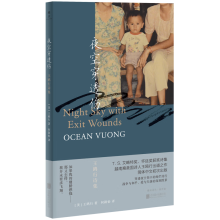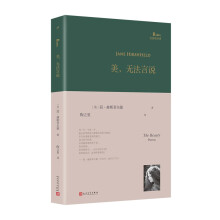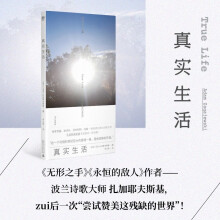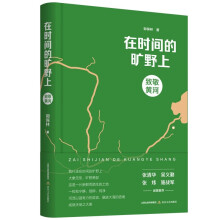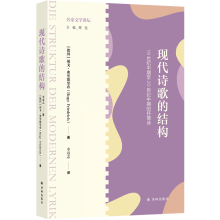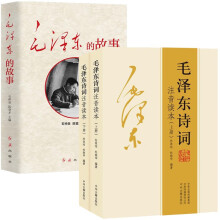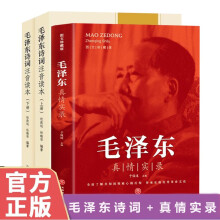《盛唐诗仙/“一带一路”人物传奇》:
“父亲,唤儿何事?”李十二急忙把剑入鞘,规规矩矩地站在父母面前。
李客并没直接回应儿子的问话,而是环顾了一下葱茏的树木和一簇一簇的繁花,开口吟道:“春国送暖百花开,迎春绽金它先来。”
这是要对诗了。这只是李客家的小儿科游戏。除了刚刚两岁,吐字不清的小女儿,三人经常随时随地对诗,有时候是吃饭时,有时候是晚睡前,有时候是早起散步时,有时候是父亲办完事一进家门……
母亲接着父亲的诗句说:“火烧叶林红霞落。”便不说了。
李十二知道这是等着自己接最后一句呢,就走到盛开的李树前,稍稍想了想,说:“李花怒放一树白。”
“一树白。”李客觉得这句着实很妙,那满树洁白的李花,不也十分地圣洁高雅吗?而开头又是一个“李”字,于是,拊掌大笑:“李白,妙啊,李白。”
“我也觉得甚妙,想想七年前,我正怀着他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相公还记不记得?”李十二的母亲莞尔一笑。
“啊,娘子说的可是太白金星那个梦?话说回来,这位上神也是我们李姓先祖啊。”
“嗯,那么小儿的字作太白如何?”李母问。
“甚好!”李客点头称赞。
从此,李十二便有了响当当的名字——李白,字太白。也许,正是冥冥中的“太白”二字,注定了李白一生对道教的求索。太白金星正是道教神仙中知名度最高的神仙之一。
三人正为这别具创意又蕴意深远的名字高兴不已,里屋传来女孩的哭声。
“女儿睡醒了。”李母急忙起身,回屋去抱女儿。
“母亲,我有名字了,妹妹叫什么呢?”李白问。
“是呀,妹妹还没有名字。你觉得给妹妹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父亲温和地望着他。
李白凑过去,看着妹妹那胖乎乎的小脸,仰头看看天,一轮白日正上中天。
李母看着他这一连串的举动,心想,难不成他要给妹妹取个与太阳有关的名字?
李白眯眯眼,手挡在眼前,从手缝里望着太阳,又把手背过去,想了一会儿:“叫月圆可好?”
李客夫妻对望一眼,均感到十分意外,看着太阳,竟然想到月亮,思维跳跃如此之大。不过也不意外,这孩子从小就想象力超常,往往在别人听上去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他也能顺理成章地联想到一起。由白天想到黑夜,看着太阳想到月亮,一点也不稀奇。
“可是,为什么要叫月圆呢?”夫妻二人想听儿子的解释,如果只是因为女儿的胖脸像一轮满月,那就太过肤浅了。
而这个时候,原本躺在妈妈怀里泪水涟涟的女儿,突然挣扎着立了起来,对着李白咯咯地笑。女孩很漂亮,有着西域人特有的深眼窝,黑黑的眼珠,长长的睫毛,白得透明的脸蛋儿。
“同为光芒之神,太阳始终如一不变,而月有亏盈满缺,像人的心情,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难过。不,不是像,月的变化正是人的心绪之变。月初不见月,当人想一件事想不明白时,内心便如漆黑无光的夜。随着思考的深入,内心一点点通透起来,正像月亮一点一点地变圆,直到满月,便想透了,心也亮了。”
夫妻二人四目相对,久久凝视着眼前这个仅仅七岁的孩子,这个看上去爱动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孩童,他是在什么时候思考出这样的问题的呢?难道是睡梦中也在思索吗?
原来李白对于月的钟爱之情,自幼年时期就已经很深了。他的一生写了很多与月有关的诗。他在人生的许多节点无不想到月。抬头望月,低头思月,卧榻想月……尤其是故乡的月。望月即是望人,思月即是思人,想月亦是想人。在李白的世界里,“月”字与“情感”是同义词。比如,他在《峨眉山月歌》中这样写家乡的月亮: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着明亮的月影。夜里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见你却难相见,恋恋不舍地去向渝州。
这是他写的家乡峨眉山的月亮。什么样的行程非要趁着月光出发呢?没办法,李白就喜欢在月光下赶路。坐在船上,晃晃悠悠,四周寂静无声,只听到船桨拨水的“哗啦哗啦”声。此时此刻,李白抬头望向夜空中的一轮明月,再看看被水波割碎的月光,便开始了想念。那么,他想念的是谁呢?为什么想见却见不到呢?这首诗是他在二十岁时写的。这个谜底就让我们去往他的年轻时代揭开吧。
……
展开